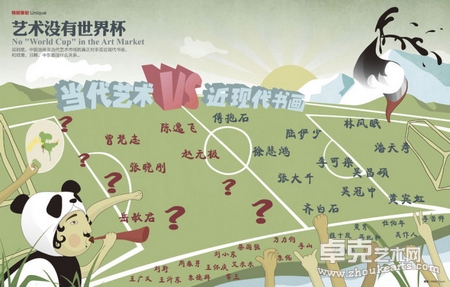为什么付羽是如此重要
我的一些零散笔记
一·年轻摄影师付羽有好几次去过罗伯特·弗兰克在纽约的家和工作室,弗兰克把自己在中国拍摄的胶卷交给付羽去冲洗。而在北京的付羽工作室,我看到了弗兰克送给付羽的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其中一张“美国人”,是弗兰克1992年自己手放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画册,在题词中,罗伯特·弗兰克把付羽称为“兄弟”。

付羽作品

罗伯特·弗兰克
罗伯特·弗兰克的妻子琼·丽芙(June Leaf),也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她有一次问客人:“知道我们为什么喜欢这个中国年轻人吗?”然后她自答道:“那是因为他每一张照片都有不对的地方。” 恕我在这儿不就此展开了,那是可以另写成千上万字的话题,你如果懂罗伯特·弗兰克,就应该会对所谓的“不对”有所领悟。
而经过李媚老师的引荐,广东美术馆收藏的数百幅庄学本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付羽手放的。

付羽作品
二·付羽之所以被罗伯特·弗兰克赏识,归根到底,还是因其作品。
每次到付羽的工作室,自然就会看到他的暗房。四月下旬,我到了付羽在宋庄的工作室,那是他不久前才搬迁过去的。我们聊得很晚。
打个比方说,摄影就好比是西餐,付羽这些年来一直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学习和实践怎么样吃这个西餐。西餐是整体的说法,里面还细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德奥、北欧、东欧等菜系,时至今日,这些菜系还有彼此交融之势。而再具体些说,什么颜色的葡萄酒配什么肉食,配什么鱼,配怎样做法的鱼和肉。还有名堂繁多的刀、叉、杯、盘、巾,使用的内容、程序和方法。更细节的还有位次、衣饰、坐相,等等。西方有腔调的人,还是很讲究这些的,看他们教育自己的儿女,是一丝不苟的。但对于我们,他们往往会很客气地说:“你们随意吃。”意思是我们可以不拘泥于这些方法,如果刀叉用不顺,可以直接用手;如果倒白兰地的杯子里灌进了威士忌,他们会比我们更感到尴尬。我并不怀疑他们的善意,他们态度是真诚的,真诚希望我们能吃点什么,别饿着。可恰恰是这样的善意,反而刺激了付羽。付羽说;“我希望能和他们一样。” 罗伯特·弗兰克、李媚等人之所以对付羽另眼相看,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年轻人,非但晓得吃什么,还很清楚怎么吃。
怎么吃是急不得的。我在日本买了本《日本写真集史,60—70年代》,很有些感触。日本摄影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摄影的民族化进程过早、过快完成了,好处就是一下子在国际上有了自己的身影,坏处则是滞胀和踯躅,达到高峰期后,日本摄影至今处在这样的状态。将来在历史上真正站得住脚的,首先是杉本博司。

罗伯特·弗兰克摄影集 《美国人》
试图理解一些思维或意识上的东西,就必须舍得点血本,必须耐得寂寞,利用所有的机会去了解它们。仅仅抓住吉光片羽是没有什么用的,要大面积地接触才能获得有效的滚动认知。付羽和朋友会在纽约一个月,天天泡博物馆、美术馆和画廊,看大量的摄影原作,从中获益巨大。比如,像罗伯特·弗兰克和黛安· 阿博丝这样的人物,给我们的印象是如此头上长角,但看过他们自己手放的原作,会发现事实远非这样简单,他们拿出来的每一张照片,单就制作工艺而言,其完成度足以让我们汗颜不已。
刘易斯·海因,给我们一直的印象是如此苦大仇深,但他的原作,那些人物的处理是那么阳光优美;Manuel Alvarez Bravo的原作也是令人咋舌的美,跟看画册完全不同,看原作才可以理解他在西方如此受尊重是有道理的;而沃克·埃文斯,当初认为他的照片需要编辑或组织,但看了原作,就单张而言,哪怕一个炉子上的痕迹,都处理的非常到位,令人叹服,每一张作为艺术品也都是成立的。
罗伯特·弗兰克、黛安· 阿博丝和罗伯特·梅普尔索普等等可以头上长角,但在制作和呈现方式上,他们遵循摄影伟大的经典传统,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你可以尽情呈现琼·丽芙所说的“不对”,但是,你所有的“不对”,必须要先过了“对”这一关。弗兰克的“美国人”是“不对”的,但你去看看他更早年拍的巴黎、威尔士、伦敦和秘鲁,看看他放印的原作而不是画册,如果你有足够的智力,就会明白“对”与“不对”的关系了。这就像齐白石说的从“不似”到“似”再到“不似”的道理。
欧美的视觉艺术学校,凡是开设摄影专业的,无不拥有设施齐全的暗房,无不拥有相关经验丰富教师的配置,无论学生将来做什么,传统基本功的修练是必经的。反观我们这里大小艺术学校,情形是正好相反。
以前学画时,李可染有句经验之谈:对待传统,要花最大功夫打进去,花最大力气打出来,方可成为大家。摄影语言,就是感知镜头能够看见的事物与能够表现出的事物之间的独特轨迹。我们常说:“我手写我心”,摄影就是“我手拍我心”,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表现的能力,这种能力,即便在今天,还是得到摄影的经典美学传统中去讨教。付羽努力做的,就是不想最终还是个野狐禅,这很重要。

付羽作品
三·二十世纪最令人敬仰的意大利画家是Giorgio Morandi,他用最清静的艺术语言创造出最有力量的作品。Morandi 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意大利度过,只去过很少几个意大利城市,唯一一次出国是去苏黎世参观塞尚的画展。在他开始艺术创作的时代,全世界的天才艺术家们都向着巴黎蜂拥而去,而他却选择了在故乡离群索居,远离艺术中心的光芒和漩涡。
终其一生,Giorgio Morandi都在自己的画室里摆弄着几十个瓶瓶罐罐。面对着这些卑微的瓶瓶罐罐,他画下了一千二百六十多张油画,此外还有大量的素描、水彩和版画。他对这些静物并非精美逼真地模仿,而是将质感、光线简化到不能再简化,对其形体的描绘,也几乎到了抽象的地步。在真和拟真之间,在具象和抽象之间,进行平凡事物中的形而上思考。评论界认为,他所关注的只是微不足道的细小题材,而反映的却是整个宇宙的状态。
当你跟一个长远的事情形成私密关系,渐渐就能从中获得一些无法预料和言传的快乐,它里面一些最奥妙的东西终将敞开胸怀。这种经历是美妙的,但需要不小的付出,尤其是耐心和时间,这时你对慢慢碾过的时间“颗粒”就会有所感知。这也是付羽向往和正在实践的。
付羽学的是雕塑,对古建筑及其营造非常有兴致,且烂熟于胸,他坚信所有这些坚固的东西,都是人们按照某种规则和形式创造出来的:他的创作和实践,就是对于确定的信念。
四·在我和付羽的闲聊中,乘机大致梳理了一下摄影史的某些章节。
首先是W.H.Fox Talbot 、Nader和Julia Margaret Gameron,其中Gameron她的肖像摄影,富有人的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然后是伟大的彼得·亨利·埃默森,看过他拍摄农民的原作,就晓得吕楠的“四季”是多么地做作,他的理念和实践成为后来“直接摄影” (Straight Photography)和“纯摄影”(Pure Photography)的基础。从埃默森出发,就会有一连串很重要的名字:James Craig Annan、Frederick H.Evans、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Bostonian F.Holland Day、Robert Demachy、Gertrude Kasebier、Clarence White、爱德华·史泰肯、Baron Adolphe De Meyer、Alvin Langdon Cobum和Frank Eugene,为什么这些人是很重要的?我就举一个例子,Bostonian F.Holland Day在1898年自扮基督的肖像,招來愤怒的指责,却启迪了后来无数的摄影师和艺术家。在这些人物之后,是奥古斯特· 桑德、爱德华·韦斯顿、保罗·斯特兰德、尤金·阿杰和Imogen Cunninghan等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1935年在美国师从过保罗·斯特兰德,Imogen Cunninghan也跟随奥古斯特·桑德学习过。
而从Alvin Langdon Cobum出发,我们又可曲径通幽到达Moholy-Nagy、Alexander Rodchenko以及Charles Sheeler,甚至是曼·雷。
至于我们一直挂在嘴上的纪实类摄影,在海因之前,可以溯源到美国非常有名的社会活动家和记者、1890年出版的《另一半人如何居住》的作者雅各布·A·里斯,甚至更早一些的罗杰·芬顿、马修·布雷迪和威廉·亨利·杰克逊, 刘易斯·海因之后,是伟大的沃克·埃文斯,他提携和深刻影响了罗伯特·弗兰克,而受弗兰克影响的,或同时代的,有黛安· 阿博丝、李·弗里德兰德,还有Bruce Davidson、Garry Winogrand,等等,我们可以看见实际上是有一条清晰脉络的。
上述这些摄影师,有多少不为我们所知?又有多少被我们误读?
我特别要指出的是另外一些名字,他们是:Manuel Alvarez Bravo、Raymond Moore、Minor White、 Harry Callahan、 Aaron Siskind 、Frederick Sommer 、Robert Adams 、Wynn Bullock和Brett Weston。 Robert Adams写有《摄影之美》和《人们为什么拍照片》。这些人几乎不为我们所熟知。他们的作品,和社会主题毫无关系,他们在摄影史上的卓越贡献,就是在形式、语言、工艺方面的不懈探索,是对摄影语言之美的不倦追寻和提炼,在我们这里,他们几乎就是玩物丧志之辈,是不值得多介绍推荐的。而在欧美地界,他们是令人瞩目的大师。我们的纪实和新闻摄影师,总以为离“战场”更近些,就能拍到好照片,殊不知,欧美的纪实和新闻摄影师,从上述大师们那里得到的教益,并不亚于从尤金·史密斯、罗伯特·卡帕那里得到的。这一方面是我们长期的、粗糙的评论和教育引导之结果,作为工具之一种,确实不需要这么精致;另一方面,也是人家让我们“随意吃”的后果,可如果我们自己不睁大眼睛,人家又有什么义务责任?
五·摄影史的任务不是单纯登记一份作品的花名册。如同各种类别的历史写作,摄影史内部隐含了复杂的权衡。具体地说,这种权衡的坐标至少包含横轴与纵轴的交叉定位。横轴指的是摄影与一个时代的互动关系;纵轴指的是摄影传统名义之下的各种承传,例如主题、语言、意象、形式、工艺技术,如此等等。通常,横轴的活跃改变了纵轴的刻度,摄影与时代的互动决定了摄影传统沿袭形式。换一句话说,前者是主动的,决定性的。文化是人类适应历史环境的产物,无论是将文化解释为一批观念体系、一种生活方式还是某些意义或者价值的认定。多元的历史环境不仅决定了文化的丰富性,同时赋予文化的调节功能。传统则积聚了一套规范,这些规范试图融入某一个地域或者某一个历史时期,于是就有了一些调节。调节使文化成为活体。从二十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中国当代摄影如何介入六十年的历史?这个问题在横轴上展开,现今看来,摄影与历史的关系远比通常想象的复杂。另一方面,相对于传统,当代摄影增添了什么?这显然是纵轴上的问题。

付羽作品
而仅仅将摄影表述为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这恐怕是一种过于简陋粗暴的想象。摄影并非历史的局外人,一个超然的记录员,而是始终镶嵌于历史之内。摄影一直企图汇集某一个历史时期最为生动鲜活的表情和心绪,同时,摄影无法逾越这个历史时期的视野局限。中国当代摄影曾经勤勉地仰望各个历史阶段的宏大主题,但是,杰作并未诞生。六十年来,中国当代摄影绝大多数作品并未赢得理想的评价。生硬僵化的主题、乏善可陈的语言和陈陈相因的想象——这些仅仅是表面症状,这一切最终证明了,这个历史时期的深刻情绪与形式、语言、修辞、意象、叙述模式等范畴脱节了。
六·不少人认为,有些中国当代摄影远离了开阔的社会历史,只有返回社会主题,摄影才能修复与公众的联系——例如关注底层的生活,或者正面强攻腐败与体制之间的关系。然而,我并不认可这种诊断书,聚集公众的目光或者因为人事的尖锐性而耸动一时,这并非摄影的胜利。因为摄影之外的某种追求而牺牲摄影,这种教训一个世纪以来已经够多了。
“文以载道”摄影理念对于个人主义的约束显然秉承了“内圣外王”的宗旨,亦即保证私人生活领域与公众社会存在转换的可能。道德限度之内的个人情志修炼甚至有利于治理社会。这是摄影、个人与社会三者的统一。然而,现代性的压力终于导致三者的破裂。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道德的控制范围,制度、契约、法律和利益成为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依据;同时,个人的权利、欲望、无意识以及种种琐碎的情绪无不表明,个人经验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区域。
在“文以载道”的理念看来,典型的基本特征是个性显现共性,或者现象显现本质。二者之间的张力愈大,摄影愈是成功。一个真正的摄影典型综合了如此之多的同类人,以至于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整个社会的结构。这就是摄影为我们提供的历史图景。
这种观点显然具有强烈的黑格尔色彩,背后很大程度依赖于总体论。这种理论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总体。大到一个阶级、一个阶层,小到一颦一笑,所有的局部都被社会有机地组织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可以从这里察觉到理论的雄心壮志:找到一个宏大的结论控制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某种程度上,摄影的典型提供了一个小号的社会模型,我们可以从这种模型之中看出历史的前景。即使我们仅仅与一个人物相遇,但是,总体论的意义就在于,利用每一个局部片断推测出总体图景。
当然,这种总体论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拒绝。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已经丧失了深度,丧失了中心,变成了各行其是的小叙事。我没有必要复述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路线,但是,我们至少要从后现代主义那里得到一个启示:历史并非单向的,每一个细节都如此必然地衔接在一起,并且显示出指定的意义。这犹如一场足球赛:一次进攻开始之后,带球,传球,过人,互相配合,如此等等,但是,这一切可能因为一个不无偶然的大脚解围而烟消云散。于是,一切如同没有发生似的——一切都重新开始。如此松散的历史过程之中,许多形象的意义是多向的,浮游不定的。
许多人至今仍对于刘易斯·海因、多萝西娅·兰格和解海龙的例子津津乐道:摄影能介入社会问题,甚至可以由此改变社会面貌。这的确令人振奋,谁都向往做个英雄,但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忽略了关键一点,这些摄影师当时身处的时代环境是媒介手段、传播方式很单薄简陋的时代,和今天的电视、网络、手机、视频铺天盖地的环境不可同日而语了。在今天,我还是要重复一下苏珊·桑塔格说的:“在不间断地接触影像和过分地接触几个一再重复出现的影像的环境下,还有什么可令人留下印象的呢?影像的震撼和影像的俗套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七·龙应台1999年5月15日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演讲,朴素而精彩,选摘如下: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见了现实背后的纵深,那么,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于“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么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惟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惟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 摄影,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八·我在一个访谈中说:所谓真实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具体而局部的时刻和空间,真实只存在于结构的联结之处,是起承转合中真切的理由和无懈可击的内心依据,是在拆解叙事模式之后仍然令我们信服的现实秩序。所以我觉得有些摄影师和评论家现在片面强调真实,诉求用照片反映真相,这可能是在极度不真实的环境中下沉时,想拼命抓住的一块木头或稻草,但这是很不可靠的木头或稻草。
希腊大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鹳鸟踟躇》开始部分,是以比雷埃夫斯事件为背景的。影片主人公,一个年轻的电视记者,在军官的陪同下来到边界岗哨了解情况。士兵排好了队等待着,他们背后是冬天的河,河那边即是别国。他们日夜守卫着边界,神经始终高度紧张。他们一个个报着名字。其中有位士兵突然穿插了一段心理独白,完全与场景不符合。他说:“恐怖的是夜里河水流动的声音。”军官未作任何评论。
在严肃的军队队列报数中,这句话的突然插入让人觉得出乎意料,不合常理。但当我们熟悉了安哲罗普洛斯不拘一格的现实主义诉求之后,就会非常钦佩这种手法。这句话是现实景象与内心现实的交叉点,内心现实从深处被挖掘出来,并与现实景象形成平行同构的状态。安哲罗普洛斯扩展了我们对于“现实”这一概念的认识。这一幕并不是什么超现实的场景,而是内心的现实主义。正因为如此,士兵报数时插入的心理独白才不是唐突的,反而是巧妙、深刻的。
所以,电影研究专家Dan Georgakas 在分析安氏电影艺术的一本著作中认为:历史是被有距离地观察着的。
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阐述和发挥了西方近代美学的“心理距离说”,他说:“东方人陡然站在西方的环境中,或是西方人陡然站在东方人的环境中,都觉得眼前事物光怪陆离,别有一种美妙风味,这就是因为那个新环境还没有变成实用的工具,一条街还没有使人一眼就看到想到银行在那里,面包店在那里……所以你能够只观照它们的形象本身,这就是说,它们和你的欲念和希冀之中还有一种适当的距离。”
九.中国摄影充斥着实用的工具性,付羽的重要,在于他对此的自觉拒斥。这种拒斥,在中国,其重要性是被严重低估的。
著名艺术史家诺曼·布列逊(Norman Bryson)有一个精辟的观点:在西方的视觉传统中,观察者如果想成为一种自足的主体,那么从一开始就得设定一种由自足的客体所构成的世界。
杰出的英国摄影师比尔·布兰特(Bill Brandt)在其1948年出版的《镜头下的伦敦》序言中这样写道:“我们大部分人都太过匆忙焦虑,太过急于证明自己,太过醉心于种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因而无法站定凝视。我们看周围的世界,也以为自己看到了。然而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偏见指引下所期待看到的一切,或是过往经历影响下而需要看到的一切,抑或是自身欲望推动下所愿意看到的一切。我们很少能将自己的思维从各种想法和情绪中解脱出来,单纯为了乐趣去看整个世界。只要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无法看到事物的本质。”
六十多年过去,布兰特这些话还是管用,不知是他目光深远呢,还是我们一直没什么长进?
何谓自足的客体?自足的客体就是不受偏见的指引、不被过往经历影响、更不会由自身欲望推动而看到的世界。站定凝视,单纯为了乐趣去看整个世界,这很理想主义吗?没有可操作性吗?未必,付羽和他的挚友卢恒、路泞、魏来、彦彰,他们志同道合,乐在其中,我能感受到这样的快乐,以及由此带来的成果。他们的追求和实践仅仅是摄影工艺层面上的吗?我看也是未必,他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尽管他们无遐也无意去顾及他人,可客观上是在匡正我们对于摄影肤浅、粗鄙、片面的理解。
单纯为了乐趣去看整个世界,就有可能看见美,看见摄影之美。这样的美,不是抽象、孤立、无生命的,在付羽他们那里,在照片中,在语言中,在呈现这些语言的工艺方式中,分明有着这样可触摸感知的美。所以,我现在可以理解付羽所说的:能在照片中闻到干草的气味,感觉到风掠过大地的声音,或者看到云层里的水汽。我们离这样的美,一直很远。应该允许、赞同、保护中国的摄影生态环境中存有这样的美,应该认真踏实补上这一课。
正如龙应台讲得那样: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美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精神领域的本体性价值之一,而不是为了什么的工具性价值。其实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的观点。全国文联早在50年代中期(1956年)就内部印发过卢卡奇(Ceorg Lukacs)美学论著,是国际学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经典之一,里面就有详细的阐述。把艺术目标泛政治化,必然落入纳粹一类极权主义精神控制窠臼,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着太多的体验和教训了。探索、追寻美,是更人性、更有力、更深刻、更久远的人生观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