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隔离时期筑起的“不安之岛”与艺术的自我疗愈
很难描述,因为那些用来描述的词语还都在下沉。我们仍处在全球后疫情的阵痛当中,惘然若失地,不得不面对世界像我们呈现出来的多重危机,人与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与发展的,人与宇宙的……
——艺术家自述

《不安之岛》(Isle of Instability)展览现场,2020
艺术家曹斐受爱彼当代艺术创作项目委任的最新多媒体装置创作《不安之岛》(Isle of Instability),在今年的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期间展出。
展览现场是两个类似居家风格的房间。这两个房间里摆放着艺术家在隔离期间的一些日常用品,如消毒洗手液、面包上的日期标签,零散的摄影作品,回国的隔离证明等等。《不安之岛》被投放在第二个房间的大屏幕上,展示着艺术家为其女儿在客厅中央随意搭建了一个迷你“岛屿”。9岁的女儿Qing饰演了岛上唯一生存的人类。

《不安之岛》(Isle of Instability)展览现场,2020
该作品受爱彼当代艺术创作项目委任,记录了艺术家在过去10个月期间因为疫情爆发与家人在新加坡公寓中隔离的经历。艺术家从个体角度出发,记录了对这段特殊的时光中的生活片段与感悟,探索隔离环境对艺术家及其家人以至于对全人类在心理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影响。

《不安之岛》(Isle of Instability)展览现场,2020
11月14日,作品展出之际,《艺术新闻/中文版》主编叶滢与艺术家曹斐和当代艺术与电影研究者、策展人杨北辰围绕该作品展开对话,从《不安之岛》出发,探讨了在这段被悬置的时空中,艺术家如何从日常和家庭生活出发,带来新的现实和人类处境的思考和创作?如何看待这段特殊时期里艺术的疗愈作用?过往的历史中,重大社会变化对艺术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艺术在这样的特殊时刻又能给激发出怎样的能量?

“隔离时期的艺术”讲座现场
《艺术新闻/中文版》主编叶滢、当代艺术家曹斐、当代艺术与电影研究者、策展人杨北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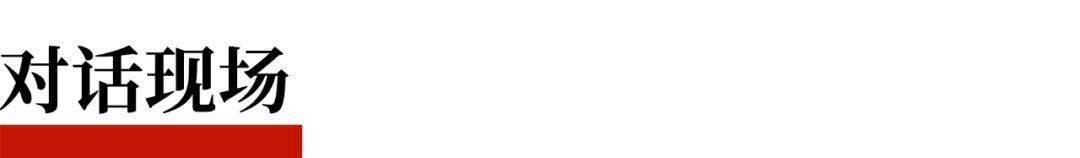
叶滢:
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在疫情期间决定创作这件作品?为什么会选择从家庭和日常生活出发进行创作?
曹斐:
去年10月我曾造访位在瑞士汝山谷的爱彼的诞生地,初步确定了以对爱彼制造业的观察为自己艺术创作的切入点。但是随着全球疫情扩散,当地工厂停工,原计划无法实现。而我也因为种种原因,被限制在新加坡的公寓里面。于是我将项目调整为在疫情期间由我来记录我所面临的个人处境以及对作为艺术家对这种状况的反应。这一想法得到了爱彼当代艺术创作项目策展人Denis Pernet先生的积极认可,爱彼认为艺术家愿意在这样的时刻去记录并呈现当下非常重要,这为我的项目创作提供了非常好的背景。

“隔离时期的艺术”讲座现场
叶滢:
当你意识到外界物理环境受限、隔离生活没有办法改变时,为什么会想到把家庭成员和生活环境转化进作品里面?
曹斐:
这些创作其实是我选择了一个观望或者放松的方式对疫情的一种速写,一种本能的反应、即刻的回应。从个人化的角度,我不想让大人的一些担忧影响小孩敏感的心灵。那段时间的现实情况,比如物资紧张等都会给幼小的心灵带来震动。我想做一些事情让小孩忘记忧虑,可以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热情。因此,对外说这个项目是疫情期间的艺术家反应,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家庭内在乐观的传递。

艺术家 曹斐
叶滢:
你在这期间记录了许多平时不会关注的日常细节,比如隔离酒店地毯边缘的一只小蘑菇、洗碗池旁边长出的一棵小豆芽等,为什么这些细节会作为敏感点会被提炼出来?
曹斐:
我之前的项目主题往往比较宏大,充满了历史的复杂性和现实的张力,但这个项目迫使我接触有限的空间,也因此思考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些小生物在某种瞬间打动了我,给予了我寓意。地毯边缘的小蘑菇让我意识到人类其实与蘑菇同处在一种菌群里面;洗碗池边的小芽,让我仿佛回到“芽与希望”传统的正能量上。当生活被真空化,依赖的东西就是眼睛能看到的东西,也因此会引发一些关于本源的思考。

隔离酒店地毯边缘的小蘑菇、洗碗池旁边长出的小豆芽
叶滢:
你对作品的表述让我想到“人类世”的概念,艺术家可能并不是有意识的去迎合某种理论,但实际上在此刻思考整个人类生存环境时,会不由自主的进入到一个新的思考角度和维度去观看我们所处的世界。请问杨北辰,作为当代艺术研究者,你怎样看待曹斐的这次创作与之前的作品的相似和不同之处?
杨北辰:
这件作品跟之前复杂性的作品相比转变很大,比如《红霞》主要呈现的对象是新中国的计算机历史,探索了一段中国科技史的变迁,发掘出了一个新的宇宙的概念;《不安之岛》其实是微型的家庭式的宇宙,但同样也有宏阔的一面。这些物件性的小细节其实一直以来也都贯穿在曹老师的创作里,即使是那些非常宏大的项目也恰恰是由非常多细小的物件组合起来的。此外,曹斐老师对于末日、灭绝以及启世录一直都有自己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早就预感到这个时刻会到来,在这个点上,《不安之岛》恰恰是与她的之前的工作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

对谈嘉宾 杨北辰
叶滢:
你之前的作品也涉及末日意识,比如在以2013年北京雾霾为主题作品《霾》里面,传达出的情绪状态非常沮丧,但当如今真正进入某种末日情境,反而带着一种生命的疗愈与解毒。同样是面对某种巨大的生态危机,创作的出发点和作品所呈现的面貌为什么会是不同的?
曹斐:
《霾》和《La Town:剧院》都是在围绕着末日情境进行创作。《La Town:剧院》是对末日情境的一个想象,通过创作脑补了这个想象,又把这个想象推到极致。所以当这场疫情来临时我反而觉得很熟悉,因为在我的作品里曾经营造过这样的一个世界,我已经在其中遭遇了心理上的恐惧,因此此刻我的创作就不仅是恐惧了,虽然我也还是会很焦虑,但是要寻找一种面对紧急状况下更加积极的求生方法。此外,从个人家庭角度讲,《霾》创作于刚生完女儿之后,家庭角色的转变在当时觉得是困难的;现在这个阶段小孩刚好长大,于是激发了我去寻求一种艺术家在极端状况下更加积极的自洽与自我疗愈的方式。

“隔离时期的艺术”讲座现场
叶滢:
面对国际艺术网络的暂时中断,我们被迫进入向内部发展的新的阶段,你对这种状态持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说你觉得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的面貌呈现出来吗?
杨北辰:
作为大事件的亲历者,很难在当下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暂时中断,而当代艺术世界恰恰是建立在全球化的宇宙政治基础之上的。无论是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的盛行导致的一系列事件,还是国家物理边界的关闭,都会促使内心相互不理解层面进一步加深。此时此刻恰恰需要我们跳出之前既定的框架去思考问题。例如,在疫情面前国境边界的概念使国家之间的关系更糟糕,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连接反而更加开放。而艺术在这个时期必然也会经受一次大的考验,这场疫情也必将进入到艺术史内部。我们回看艺术史,每一次的瘟疫或者大的战争,其实都深入其内部,从阿尔弗雷德·丢勒的《天启四骑士》、彼得·勃鲁盖尔的《死神之舞》,到爱德华·蒙克的《西班牙大流感》,再到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的关于艾滋病的作品,这些瘟疫和疾病都进入到了艺术家的工作里,成为了我们可能铭记这些历史事件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而这恰恰是艺术家在这个阶段可以做的工作。
叶滢:
在特殊时空环境下,怎样用艺术的角度打开另外一个可以想象和创造的空间?
曹斐:
对我个人来说,这种创作就是我对这种特殊时空的回应。我希望自己可以用一种非常放松的方式,去掉复杂的程序,在制作层面上用到最简单的方法来进行创作。作为艺术家不是要解读这个时代,或者用非常精英的眼光去看待这个时代,而是应该用一种打开的方式迎接变化的处境,不受一时一地困境的限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同呼吸或者再发现。对于观众来说艺术家的这种自我疗愈希望也能对他们起到某种疗愈,找到一种跟世界共处的方式。

“隔离时期的艺术”讲座现场

现场观众:
这部作品很多细节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在完成了作品之后您自己有更强烈的不安,还是得到了很多安宁?或者说得到了自己对于之前一些思考的一种回答?
曹斐:
回到中国后其实很安心,有点逃脱了“不安之岛”的感觉。回望这部作品,从家庭角度出发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如果它是一个家庭录影带,放在女儿长大以后再回看作品,对家庭来说它是感人的。就像我父母是雕塑家,在我半岁时就开始给我做过一些塑像,他们用塑像的方式凝聚情感,来表达对孩子的爱。《不安之岛》从作品上来说传达了这样一种不安,但是从时间跨度上看,也是一种家庭内部的传递。

“隔离时期的艺术”讲座现场观众提问环节
现场观众:
在您的眼中艺术家、哲学家在面对灾难面前会带给我们什么?
杨北辰:
艺术家往往有一种天然的直觉,就像曹老师刚才提到自己曾经想象预演过一次危机的场景,所以当危机真正到来的时候,剩下的都是生活、情感以及具体的时刻。哲学家的思考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去预见未来,但当危机真正到来时,只能调用过去的知识做出判断。而在现实的经验面前,这些判断往往只是在重复他们之前的观点。艺术家的工作是充满想象力的、直觉的、身体的,他们的敏感度、弹性和柔韧性都会使得他们的工作和这个世界的某种本质进行连通,这是哲学家的理性思考所无法取代的。艺术家不能检验对错真假,但有一种更本质性的力量,可以给予我们很多的启示。
或许,我们都应该感谢疫情,接受这份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人在宇宙间陷入迷茫,在孤独中审思。
——艺术家自述
*图片由艺术家与爱彼共同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