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智:响堂山石窟东魏至北齐石刻佛像造型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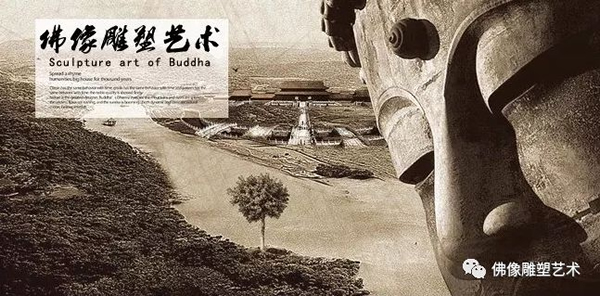
黄文智
博士,天津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雕塑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雕塑理论。
响堂山石窟包括北响堂、南响堂、水浴寺(小响堂)石窟,该石窟群位处邯郸市南部,与安阳市比邻。邯郸与安阳两地在春秋战国至隋代均为邺城辖地。邺城为六朝古都,因此又称邺都。东魏、北齐时的邺都由高氏家族把持朝政,其时朝野奉佛之风极为兴盛,佛教及佛教美术继北魏中晚期以后再次获得大发展,掀起了新一轮的造像高潮,留存至今的石窟寺造像、单体石刻造像不仅数量众多,且雕刻精美。此中,与皇家贵胄关联的响堂山石窟最具代表性。
对响堂山石窟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初,最初有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先后三次考察响堂山石窟,日本学者长广敏雄和水野清一在此基础上于 1937 年对响堂山石窟作了更深入的调查。1935 年, 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考古组多位专家考察响堂山石窟,出版《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尗子对南、北响堂山石窟作了相对详细的记录,马忠理就响堂山石窟的造像和刻经撰文发表。围绕响堂山石窟的建筑、造像、分期、刻经等问题,赵立春、刘东光、李裕群、唐仲明均有研究成果面世,陈悦新则阐述了响堂山石窟的佛衣类型,此外还有专门针对海外流失响堂山石窟造像展开研究者 。近些年,也出现了一些关涉响堂山石窟的硕士论文。2014 年,《中国美术全集·雕塑卷·响堂山石窟》出版 ,系统阐述了响堂山石窟的历史地理背景、现状及相关研究成果,赵立春用较大篇幅阐述了石窟造像艺术的风格、题材、装饰纹样及破坏和流失情况。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还专设响堂山石窟项目,为研究者提供便利。上述成果,主要集中在石窟开凿的社会背景、造像分期、建筑形式、刻经内涵,以及一些附属图像及装饰纹样等问题上, 对于石窟造像微观造型样式变化、与同区域单体造像之间的横向比较等问题,尚有进一步探讨空间,尤其是佛像造型样式的梳理,会影响到石窟造像年代的辨识和分期结果。
本文以狭义的佛像(佛陀)为研究对象。佛像是佛教建筑空间的中心所在,也是信徒礼拜和匠师极力雕刻的对象,因此佛像造型样式的变化能够相对客观反映当时造像理念的变迁,有助于造像年代的判定。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采用考古类型学与艺术史样式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主要探讨响堂山石窟佛像的着衣形式和雕刻样式的变化规律,以及这些佛像与周边区域单体造像之间的关联,以期在造型变化和断代分期上对该石窟龛像获得更深入的认识。
按照袈裟形式的不同,本文将响堂山石窟北齐石刻佛像分为四组来讨论。

一、第一组佛像
第一组佛像为响堂山较早开凿的龛像,实例少,其着衣形式与衣褶雕刻样式均与河北中南部地区同期实例相仿。

如北响堂第六窟正壁佛像(图 1 ),跏趺坐于亚字形台座上,头部残损,着衣相对完整,左领襟下垂(以物象自身为准区分左右,下同),右领襟下垂至胸腹部后敷搭在左肩上,两领襟围合成 U 字形, 其间露出自左肩斜向右胁的僧衹支(内衣)。双腿部分衣装贴体,有较短的覆座悬裳,下垂衣襟外缘 有 S 形内外翻转结构。袈裟衣褶作双勾阴线表现,双勾阴线中间有剖面为三角形的凸棱线,两臂上两组双勾阴线间有粗大棱状线,整体形成了双勾阴线与大棱状线组合的衣褶雕刻样式。
在河北、山东地区,领襟围合成 U 字形的较早纪年实例见于青州龙兴寺遗址北魏孝庄帝永安三年(530 年)贾淑姿造像。此种袈裟领襟的围合造型由北魏晚期以来双领下垂式袈裟演变而来,特征是双领下垂式袈裟的右领襟由原来披搭于左臂上升至左肩,领口变小,胸部束带随之趋于弱化和消失。
着这种变化形态佛装的佛像在东魏后段至北齐时实例众多,单独名为敷搭左肩式袈裟 。北响堂第六窟正壁佛像的覆座悬裳自然下垂,并不似典型北齐佛坐像那般短,其形态与临漳北吴庄出土东魏武定四年(546 年)佛像颇为相似,区别是后者下垂衣襟要厚实些。双勾阴线与大棱状线组合的衣褶是该地区北魏孝明帝正光年(520—525 年)以来流行的衣褶雕刻样式,实例见于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东魏石刻佛像。北响堂第六窟正壁佛像袈裟衣褶作如是表现,应该是吸收了曲阳白石造像的雕刻样式, 曲阳白石造像生产地实际上也是北魏晚期以来河北、山东造像中心之一。此外,主尊佛像两侧的弟子和胁侍菩萨像,在临漳邺城遗址出土的东魏后期白石造像中可以找到不少造型相似者。

综合上述造型特征,可推测北响堂第六窟正壁佛像的开凿时间应该在东魏,是响堂山石窟群中年代最早的龛像。该窟位于第四窟(释迦洞)上部右壁山崖上(图 2,白色方框内人工垒砌小屋内即第六窟),坐北朝南,造像龛及附属图像皆沿崖面开凿。其左壁为山体,前壁和右壁为砖石垒砌,正壁上方有四个榫眼,原应存在木构建筑。第六窟造像龛没有开凿在拥有更大崖面的东壁, 而是选择了面积不大但靠北凸出来的崖面上,应该是有意遵循寺院坐北朝南的一般做法。该窟这一位置和朝向,与其下方几个学界公认较早开凿的大型洞窟不同,后者包括第三窟(刻经洞)、第四窟(释迦洞)、第九窟(大佛洞) 在内,均在同一高度崖面上,大体上坐东面西。再从石窟地层的角度看,第六窟前面原来应该有较大的地面空间,但现在比较狭窄,且缺乏进入此窟的台阶或路径(游客不能进入此窟参观)。窟前有大 面积人工斩山痕迹,应该是开凿规模巨大的第四窟时留下的,破坏了第六窟前的平台(可能进入此窟的台阶或路径也被斩去了),据此可推测第四窟晚于第六窟开凿。此外,北响堂常乐寺的金海陵王正隆四年(1159 年)《鼓山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记》碑记载 :“文宣(高洋)常自邺都至晋阳,往来山下……于此山腹,见数百圣僧行道,遂开三石室,刻诸尊像,因建此寺”,表明了在北响堂山三大窟开凿之前,山腹中有僧人活动,说明此地应该有石窟或寺院存在,其中可能就包括了当前的第六窟。

图 4 北响堂第九窟中心柱正壁佛像

图 5 北响堂第九窟中心柱右壁佛像
北响堂山第八窟正壁主尊佛像,头、手和覆座悬裳均已不存,但袈裟的基本形式和衣褶雕刻样式清晰可辨(图 3),领襟披搭形式与第六窟正壁佛像一致,衣褶为双勾阴线,双线间有剖面为三角形的凸棱线(凸棱线有一定程度风化),这些特征与第六窟正壁佛像高度相近。衣褶作双勾阴线表现的实例在河北中南部东魏后期至北齐颇为常见,如前述临漳北吴庄出土东魏武定四年(546 年)佛像、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东魏兴和三年(541 年)李晦造像⑨、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东魏武定五年(547 年) 张同柱造像⑩。结合佛像袈裟右领襟披搭在左肩和衣褶雕刻样式的特征,响堂山第八窟正壁主尊佛像的年代应稍晚于第六窟主尊佛像,但可归为同一组别,完成时间或为北齐初。
二、第二组佛像
第二组佛像的实例为响堂山石窟大型皇家窟龛中的主尊佛像,尺寸高大, 着通肩式袈裟,衣褶雕刻亦与河北中南部地区同期实例存在关联。

如北响堂山第九窟中心柱正壁佛像(图 4)、第九窟中心柱右壁佛像(图5)、第四窟中心柱正壁佛像(图 6),三像皆着通肩式袈裟,除第九窟中心柱右壁佛像外,余两像跏趺坐。第九窟中心柱正壁佛像、第九窟中心柱右壁佛像面部有后世重新敷塑痕迹,第四窟中心柱正壁佛像整体保存相对较好, 但头部是后人补刻。三像最显著特征是通肩式袈裟衣褶的雕刻样式,都以胸部为中心呈 U 字形展开, 其起伏关系为剖面作一高一低组合的粗大棱状,形成富于层次感的视觉效果。
这种高低棱状组合的衣褶样式与前述北响堂第六窟正壁主尊佛像颇为相似,区别在于第六窟佛像衣褶中双勾阴线内的凸棱线较为细小,而北响堂山第九窟中心柱正壁佛像、第九窟中心柱右壁佛像、第四窟中心柱正壁佛像中双勾阴线的距离被有意扩大,使得两线间的凸棱随之宽大起来。可以看出, 这三尊佛像袈裟衣褶雕刻样式,应是融合了河北中南部佛像凸棱状衣褶和双勾阴线衣褶两种造型特征而形成,故宫博物院古代雕塑馆藏一尊高大白石佛像残躯(一佛两胁侍组合)的袈裟衣褶也是这般表现(图 7),不同之处是故宫藏白石佛像袈裟形式是敷搭左肩式袈裟。故宫实例虽无明确的出土地信息 l,但这种尺寸高大、雕刻精美的白石造像,可能出自于东魏北齐时期河北中南部的某所皇家寺院。上的洞穴。一些学者凭此认为第九窟开凿于东魏,但也有学者根据造像样式和文献记载,认为第九窟开凿于北齐。先不论第九窟上面的洞穴是否为高欢瘗埋之所,就第九窟中心柱正壁佛像的袈裟衣褶特征而言,应该是在河北中南部佛像凸棱状与双勾阴线衣褶融合后出现的,再结合其跏趺坐双腿下悬裳极为短促的情形(这一特征与东魏佛坐像覆座悬裳区别明显),该像应为北齐初完成。第四窟中心柱正壁佛像造型特征与第九窟中心柱正壁佛像基本一致,为同期之作。
三、第三组佛像
第三组佛像仅一例,同为北响堂山皇家大型窟龛中的主尊佛像,袈裟形式较为特殊,衣褶雕刻样式与同窟其他主尊佛像一致。
北响堂山第九窟中心柱左壁佛像(图 8),倚坐像,脸部尚存后人用泥敷塑痕迹,双手残缺。佛像外层袈裟左领襟下垂,右领襟半覆右肩后下垂至右臂肘部,再左转披搭于左肩。中层佛装左领襟下垂,右领襟自右肩下垂至腹部,再绕右臂后反折插入腹部外层袈裟领襟内。内层佛衣是自左肩斜向右胁的僧衹支,胸腹部有系缚僧衹支的绳带。袈裟衣褶表现为粗大的双勾阴线,造型特征与同窟中心柱另两尊佛像相似。
陈悦新将这种颇为复杂的领襟披搭形式佛装称为中衣搭肘式佛衣,不过这种着衣形式与后述典型中衣搭肘式佛装有差异,故单独名为右肩半披中衣搭肘式佛装。陈悦新认为中衣搭肘式佛装源流与南朝开凿的南京栖霞山石窟和云冈第三期洞窟实例相关联。但就佛像衣装演变规律而言,笔者认为这种复杂的领襟披搭形式似与洛阳龙门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关系更为密切。北响堂山第九窟中心柱左壁佛像的外层袈裟,
可视作右肩半披式袈裟, 龙门宾阳中洞正壁主尊佛像亦外披这种袈裟(区别是该像右领襟披搭于左臂而不是左肩),中层佛装为双领下垂式袈裟,由此形成两层袈裟叠加表现的新造型。这种新型佛像,集中分布在龙门北魏大中型窟龛正壁(西壁) 和巩义主要石窟主尊位置上,可能是当时皇家或位高权重者所重的佛像样式 。

天龙山第二、三窟正壁佛像(图 9)大体上也是在宾阳中洞主尊佛像两层佛衣叠加形式基础上变化而来,区别是天龙山实例右臂下垂衣襟下缘反折插入腹部外层袈裟领襟内,覆座悬裳也略有变化。天龙山实例继承龙门石窟这种高规格佛像样式,或许与该窟功德主为高氏家族有关 。
北响堂山第九窟中心柱左壁佛像的着衣形式,与天龙山第二、三窟正壁主尊佛像造型颇为相似, 尤其是后者外层右肩半披的结构,和右臂衣襟下垂反折插于腹部外层领襟内的穿插形式,应为北响堂佛像的前期样式。东魏北齐时邺城与晋阳(今太原)之间对等的政治地位和密切的交通,使得两地的佛教造像应该存在深层次的关联。因此可以推测,北响堂山第九窟中心柱左壁佛像应该是在天龙山第一期佛像着衣形式基础上变化而来的。
北响堂山第九窟中心柱左壁佛像着衣形式虽然与同窟中心柱其他壁面佛像不同,但属于石窟内整体完成之作,且局部袈裟衣褶雕刻样式一致,为同期完成。
四、第四组佛像
第四组佛像数量最多,广泛分布在北响堂山、南响堂山和水浴寺石窟中,佛衣造型在北响堂山第九窟中
心柱左壁佛像基础上变化而来,为中衣搭时式佛装,衣装贴身表现,衣褶雕刻存在多种样式。根据外层袈裟右领襟披搭位置的不同,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右领襟披搭在左臂,二是右领襟披搭在左肩。

右领襟披搭在左臂的实例如北响堂山第三窟主室正壁佛像(图 10)、第三窟主室右壁佛像(图 11)、第一窟右壁佛像(图 12),皆跏趺坐,头部残失(第三窟主室右壁佛像头部为后世修补),左右手分别施与愿、无畏印。三像着衣形式与北响堂第九窟中心柱左壁佛像接近,不同之处是这三像右领襟没有半披右肩,而是自左肩经背部斜向右胁下,再绕前腹披搭在左臂上,僧衹支上没有束带的痕迹。三像跏趺坐双腿下皆有短小外延衣襟,未覆坛。衣装完全贴身表现,显得质地轻薄,衣褶以疏朗的线刻为主,第三窟主室右壁佛像两臂处衣褶还保留有双勾阴线特征,但袈裟表面整体平整,已脱离了第一、二组佛像注重衣褶浮雕凸起的样式。袈裟领襟和衣装质感、衣褶雕刻样式的变化,说明三尊佛像与前述第三组佛像在袈裟形式上虽存在关联,但在雕刻样式上有明显区别,分属于不同完工年代。
北响堂山第三窟又称南洞、刻经洞,窟外有《唐邕写经碑》,记载了窟内刻经起止时间为北齐后主天统四年(568 年)至武平三年(572 年),据此可推测该窟开凿时间早于北齐天统四年,可能为北齐武成帝时期(561—565 年)。

佛像袈裟右领襟披搭在左肩的实例主要分布在南响堂山和水浴寺,如南响堂第一窟中心柱正面佛像(图 13)、南响堂第五窟正壁佛像(图 14)、南响堂第七窟主室正壁佛像(图 15)、水浴寺西窟中心柱正面佛像(图 16)、水浴寺西窟中心柱左侧面佛像(图 17)。五例佛像皆跏趺坐,大多数头部不存。佛像左右手分别施与愿、无畏印(南响堂第一窟中心柱正面佛像右手为后世修补),人物坐姿、手印高度统一。五例佛像外层

袈裟披搭形式与同组北响堂山石窟实例一致,中层佛装右领襟自右肩下垂至跏趺坐双腿处, 再披搭在右臂上,右臂下垂衣襟并没有反折插入外层胸腹部领襟内(南响堂第七窟主室正壁佛像右领襟在胸部部分折入外层袈裟右领襟内,但与前述佛像领襟穿插关系有所区别)。五像中除南响堂第七窟主室正壁佛像、水浴寺西窟中心柱正面佛像外,余三像僧衹支胸腹部有系缚束带的褶皱,但不见束带垂下。这几尊佛像跏趺坐双腿处皆有短小外沿衣襟,特征与同组前三例佛像一致。佛像衣装质感较为轻薄,衣褶雕刻略有差异, 南响堂第一窟中心柱正面佛像衣褶为疏朗的阴线刻 ;南响堂第五窟正壁佛像上半身衣装表面作磨光表现,双腿处衣褶有双勾阴线特征 ;南响堂第七窟主室正壁佛像两臂衣褶为疏朗的片形阶梯状,双腿处衣褶磨光无纹 ;水浴寺西窟中心柱正面佛像、水浴寺西窟中心柱左侧面佛像亦以阴线刻为主,造型趋于简洁。这种局部雕刻样式的变化,显示出同一时期、同一空间内个体佛像之间的细微差异。

南响堂除了上述代表性实例外,还有一些倚坐像需要提及。如南响堂第五窟北壁佛像(图 18)、南响堂第七窟主室南壁佛像,两像人物姿势完全一致,着衣形式高度相似,衣装贴身表现,袈裟表面大部分磨光,仅有少数几条阴线刻衣褶。两像衣装造型特征与前述同组跏趺坐佛像并无明显差异, 显然是基于同一造像理念而雕刻。
南响堂第二窟外壁摩崖上《滏山石窟之碑》记载 :“有灵化寺比丘慧义……于齐国天统元年乙酉之岁,斩此石山,兴建图庙。时有国大丞相淮阴王高那阿肱……广舍珍爱之财,开此□□之窟。”该碑为隋代所立,据碑文可知第二窟开凿时间为北齐天统元年(565 年)。另外,水浴寺西窟内有北齐武平五年(574 年)题记 。据此可知,南响堂石窟和水浴寺石窟这几尊佛像的开凿年代与同组北响堂佛像相近,可归为同期开凿。
五、四组佛像的开凿年代和造型样式的变化规律
第一组佛像年代早至东魏,其造型特征可与河北曲阳、邺城同期石刻佛像相类比。这种结果与学界以往观点有所区别,多数学者认为响堂山开凿最早的洞窟是第九窟,该窟被认为是北齐高祖高欢瘗
埋之所。文献记载,高欢于东魏武定五年(547 年)卒,葬于漳水之西,在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鼓山就是现在的北响堂山所在地。这就是说,在东魏武定五年时,该地就有石窟寺了,此石窟寺有可能就是北响堂山第六窟。如前所述,第六窟除了主尊佛像造型具备东魏特征外,其窟在朝向、地理位置上与三大石窟均不同,且从层位关系上看,第四窟打破了第六窟前平台的空间,存在先后次第关系。据此可推断第六窟的开凿年代在第九窟、第四窟之前。
第二组实例为北响堂山第九窟、第四窟中的主尊佛像,这两窟分别是北响堂山石窟中的最大和位处中间位置的洞窟,皆作中心柱式结构,主尊佛像袈裟衣褶雕刻样式在第一组佛像双勾阴线衣褶基础上,形成剖面作一高一低的三角形棱状组合,显得质地很厚重,其年代当在北齐前期。这种颇为费时费力的衣褶雕刻样式并没有广泛流行起来,只见于河北中南部少数较大的石刻佛像中。
第三组佛像仅有一例,为第九窟中心柱左壁佛像,其着衣形式较为特殊,与天龙山第一期龛像应有内在关联。佛像袈裟衣褶表现为粗大的双勾阴线与棱状线相结合,显得质感厚重,和同窟中心柱其他壁面佛像造型特征相似,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完成的。这种新式佛装形成后,对此后佛像的着衣形式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可以说,第九窟中心柱左壁佛像的佛衣是一种承前启后的佛装形式。
第四组佛像着衣形式是在第三组佛像基础上变化而来的,衣褶雕刻存在单勾阴线、双勾阴线、片形阶梯状、素面无纹和凸棱线五种样式,这些雕刻样式都可以在河北中南部北齐石刻佛像中找到大量相似实例,体现出当时热烈的造像风潮和富有变化的雕刻技法。相对前三组实例而言,该组佛像衣装质感有较大改变,皆贴身表现,这是北齐时期佛像的典型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该组北响堂山佛像躯体方圆厚实,尤其是两肩轮廓线相对硬朗,南响堂和水浴寺佛像虽然躯体同样壮实,但肩部轮廓线相对圆润一些。
将上述佛像试作分期如表 1。第一组佛像中的北响堂第六窟正壁主尊佛像完工年代在东魏,北响堂第八窟正壁佛像年代稍晚, 或为北齐初。两像存在诸多相似点,后者是在前者影响下完成的,因此同归为第一期,年代为东魏后期至北齐初(约 540—555 年)。第二组、第三组佛像集中在北响堂第九、第四窟中心柱佛龛内,包括通肩式袈裟与右肩半披中衣搭肘式佛衣两种着衣形式,为同期完成,归为第二期,年代为北齐前期(约 550—560年)。第四组佛像分布在南响堂和水浴寺石窟中,佛装形式基本相同, 且有明确纪年,同属第三期,年代为北齐中后期(561—577 年)。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响堂山石窟的开凿过程和造型样式的变化规律,其中对于东魏实例的确认和石窟造像重新分期的观点,与学界以往认识有差异,对佛装衣褶雕刻样式的梳理则有助于加深对响堂山石窟造像的进一步认识。
余论
学界认为,包括响堂山石窟在内的河北中南部北齐石刻佛像,皆受到来自于西域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印度笈多造像样式影响,不过,这种影响的结果是选择性的。上文提及的四组佛像着衣形式中,敷搭左肩式袈裟是双领下垂式袈裟的后续形式 ;右肩半披中衣搭肘式佛装或在洛阳龙门和太原天龙山石窟龛像基础上演变而来,此佛装继续发展为北齐典型的中衣搭肘式佛装 ;只有第二组佛像通肩式袈裟的出现,或许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印度笈多造像存在关联s,但其衣褶雕刻却完全是本土雕刻工艺。第四组佛像衣装质地轻薄,皆贴体表现,人物躯体特征有一定呈现,这种造型特征应该是来自于印度笈多朝造像样式的影响,其所传路线应是海路t。可见,响堂山窟龛佛像的着衣形式依然是在本土造型基础上的自我发展,但有部分胁侍菩萨接受了印度笈多朝注重人物肌体表现的造型
特征。如北响堂第六窟佛龛右胁侍菩萨 u、第九窟中心柱左壁龛左胁侍菩萨(图 19),两像皆裸露上身,身上璎珞、披帛皆简略,下身两层裙裳皆贴身表现,这些特征均与典型的笈多朝佛像相近。第九窟胁侍菩萨出现了左腿弯曲、右腿直立的动态,臀部和腰部也因此产生了曲线美,这与印度女神像“三曲法”的动态颇为相似。因此,北响堂山龛像出现了诸多新造像特征的同时,接受印度笈多朝造像因素主要体现在菩萨造像上,整体呈现不平衡性。
北齐之世,皇室立寺四十三所 v,邺都有寺约四千所,僧尼八万人(《续高僧传》卷十《靖嵩传》),全国有僧尼二百余万(《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北齐的这种崇佛之风甚至比北魏迁都以后的洛阳时代还要强烈 w,因此,东魏北齐时期,先后作为实际掌权者和皇家的高氏家族延续了北魏帝王家的崇佛传统,先是在太原天龙山开窟造像,迁都邺城后又在都城周边的南、北响堂山镌刻佛国天宫盛景。
相对于北魏晚期的洛阳时代而言,北齐时邺都除了皇家和重臣有持续开凿石窟的热情外,世俗的信徒似乎更热衷于制作体量相对较小的单体石刻造像,尤其是使用产于太行山东麓沿线的白色大理石(俗称汉白玉)制作的佛像,受到热烈追捧,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造像形式。其中以邺城地区佛寺遗址或窖藏坑出土的造像最为精美,有学者根据这些出土造像的造型特征提出“邺城模式”一说。不过这种“邺城模式”似乎没有关涉响堂山石窟造像,而只限于以背屏式为基本特征的单体造像。实际上, 这些白石材质单体造像的人物造型特征,与南、北响堂山石窟中龛像比较接近,只是白石造像更好地利用了白石质地细腻和易于雕刻的特点,在人物背景和附属装饰上穷尽工巧,创作出极具视觉愉悦感的“龙树背龛式”造像 。从中可以看出,相对在山间开窟造像而言,简便且具视觉愉悦感的白石造像能够更好地满足信众的审美需求,这也是该时期白石佛像能够获得大发展的根本原因。
北齐时期的佛教与皇权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佛教势力由此过分膨胀起来,这是彼时开窟造像之风盛行的主要条件,也是导致北齐政权在较短时间内分崩瓦解的重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了解了响堂山石窟开凿历程和文化内涵,也就更好地理解了北朝晚期东部地区社会发展的历史图景。
附记 :笔者于 2020年 10月 18—21 日参加洛阳“龙门石窟申遗成功 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宣读本文主要观点后,与会的响堂山石窟博物馆馆长赵立春老师指出第六窟的地理位置、其与第四窟的层位打破关系需要着重阐述,使本文得以完善。又承蒙赵老师提供北响堂常乐寺的金正隆四年(1159 年)《鼓山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记》碑文出处,对本文起到重要补充作用。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张建宇教授也对本文提出建设性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原文刊发于《艺术探索》2021年第4期,此处为摘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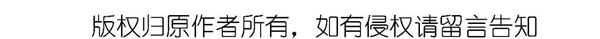

长按关注:[佛像雕塑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