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0年来的行为艺术如何诉说着性暴力的创伤?

莱斯利·拉博维兹的行为艺术《强奸的迷思》(Myths of Rape) 图片来源:Susanne Lacy/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The New Republic
1971年,美国艺术家苏珊妮·莱西(Suzanne Lacy)和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一起在加州艺术学院上课,当时她有了一个想法:如果进行一场行为艺术表演,让观众听一段女性讲述被强奸故事的录音,会怎么样?这在如今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但在当时并不简单,因为还从未有过受害者讲述自己的故事。南锡·普林森塔尔(Nancy Princenthal)在她的新书《不可言说的行为: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艺术和性暴力》中写道,莱西和芝加哥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找到愿意发声的受害者。“这些女人很难找,”莱西说,“她们大多不想发声,多年来把遭受强奸的经历藏在心底,一直瞒着家人、朋友,甚至丈夫……恐惧变得像呼吸一样自然。”
莱西和芝加哥最终找到了7位女性,她们的录音也成为了1972年行为艺术表演《洗礼》(Ablutions)的一部分。这件行为艺术作品是与艺术家桑德拉·奥格尔(Sandra Orgel)和阿维娃·拉赫马尼(Aviva Rahmani)合作完成的,包括一系列仪式动作:莱西和另一位表演者在墙上钉了50个牛腰。一个裸体女人像木乃伊一样被绑在椅子上。另外两名裸体女子在分别装满生鸡蛋、牛肉血和灰色粘土的浴盆中沐浴,然后身体用白色床单包裹起来。两个表演者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把所有的东西都用绳子捆在一起。在这整个过程中,在这些抽象的、象征性的意象之上,萦绕着七个匿名女性的言语录音,她们用痛苦的细节描述了自己是如何被强奸的。“我感到很无助,” 最后一个声音说道,“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躺在那里,小声地哭了起来。”

《洗礼》 图片来源:suzannelacy
这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时刻——正如费雯·格林·弗里德(Vivien Green Fryd)在她的新书《违背我们的意愿:1970年以来美国艺术中的性创伤》(Against Our Will: Sexual Trauma in American Art Since 1970)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性创伤最早的公开见证之一”。的确,这件行为艺术作品标志着文化史上一个安静的转折点:女性开始公开谈论自己的身体,谈论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情和遭遇。但关键的是,她们不仅仅是在讲述,还把她们的创伤转化为一种奇怪的新表现形式,一种难以理解的、多感官的困境,普林森塔尔称之为“对连贯性的进攻”。“当面对着对她们的经历和情感毫无兴趣也没有合适词汇描述的父权制体系和结构时,她们用自己的创造力进行清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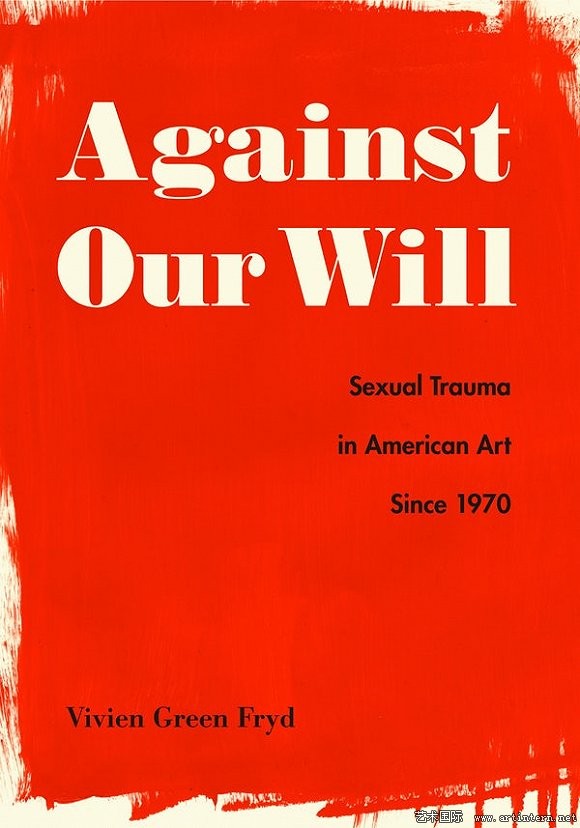
《违背我们的意愿:1970年以来美国艺术中的性创伤》
在另一个清算的时代,弗里德和普林森塔尔的书令人信服地将行为艺术与性暴力联系在一起,改写了行为艺术的历史。现在读这些书,既有启发性也有痛苦,因为它们尖锐地提醒我们,自那之后的几十年里我们已经走了多远,却依然深陷在同样的问题中。其中最突出的是早期女性行为艺术家的无畏精神,以及她们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今天对艺术的看法。她们在面对创伤时没有将创伤外化,而是把她们的身体变成了艺术材料。她们坚持认为,艺术关乎的不是完美的图像、卓越的过程,抑或是想法的施行,而是在根深蒂固的印象和世俗的镇压下,传递有时甚至语无伦次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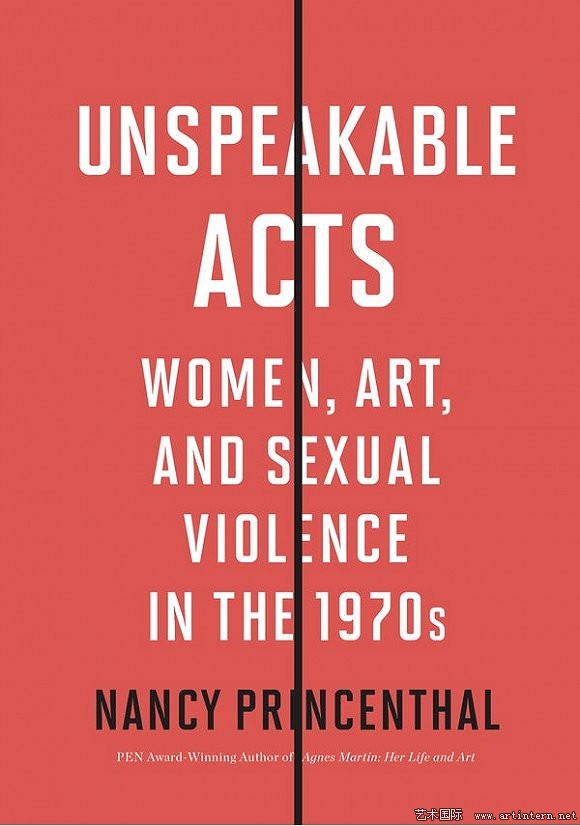
《不可言说的行为: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艺术和性暴力》
行为艺术起源于未来主义戏剧和达达主义卡巴莱歌舞表演,但我们熟知的西方行为艺术开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艺术家和诗人开始与音乐家和舞蹈家共事,创造了一种跨领域的合作。比如,美国艺术家阿兰·卡普洛(Allan Kaprow)策划的“即兴表演”(Happenings),这个词比较随意,指的是各种荒唐的表演,从女人舔汽车上的果酱到杂耍剧场里的即兴表演。激浪派(Fluxus group)艺术家也基于各自的理念进行行为艺术的创作,比如艾莉森·诺尔斯(Alison Knowles)制作的《做沙拉》(Make a Salad)。

艾莉森·诺尔斯的行为艺术《做沙拉》 图片来源:artsy
尽管听起来很荒谬,但这些早期的行为艺术有一个明确的存在理由:测试某事可被视为艺术的可能性。有时可能是他们的即兴创作,但通常是围绕着艺术家构思的一系列行为,或是身体力行的参与,这种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开放心态,给了行为艺术额外的优势。对创作者来说如此,对观众来说更是如此,行为艺术让他们不仅可以观看,更加可以参与,成为打破艺术和生活之间的隔阂的一部分。
而随着行为艺术的发展,这一体裁也变得更专注于自我反思,人们开始用行为艺术来探索现实和身体极限。而这有时会表现在人的权利赋予上,特别是对于那些想要改变和庆祝自己性别的女性,但也经常带来暴力和侵犯的隐患。而这类行为艺术中最著名的是由男性创作的:1971年,克里斯·波顿(Chris Burden)让一个朋友朝他的胳膊开枪;三年后,他被短暂地钉在一辆大众甲壳虫的引擎盖上。在维托·阿肯锡(Vito Acconci)1969年的行为艺术作品《跟踪》(Following Piece)中,他会对随机选择的陌生人进行追踪,直到他们进入一个私人空间。在阿肯锡1972年的行为艺术作品《温床》(Seedbed)中,他在纽约苏荷地区索纳班画廊(Sonnabend Gallery)的地板下制造了一个伪装,使其可以带着麦克风藏身于此,当人们坐在他上边时对他们说话,同时自慰。

克里斯·波顿的行为艺术 图片来源:BBC

维托·阿肯锡的行为艺术《温床》 图片来源:artda
有些女性行为艺术家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创作,但不同于波顿的虚张声势和阿肯锡令人毛骨悚然的控制欲,对于那些将自己的身体置于危险境地的女性艺术家来说,选择本来就更加复杂和令人担忧。作为女性的她们经常遭遇性暴力的威胁,不管这是否是原本明确的主题。
这一点在小野洋子1964年的里程碑式行为艺术作品《切片》(Cut Piece)中得到了体现。小野洋子也是一位激浪派艺术家,而《切片》这一行为艺术作品如下:
表演者坐在舞台上,面前放着一把剪刀。观众可以一个一个地上台,从表演者的衣服上剪下一小块带走。表演者在整个过程中保持不动,可以自主选择结束的时机。
正如南锡·普林森塔尔在书中所叙述的,在小野洋子前两场在日本的行为艺术演出上,观众们表现得相当克制——除了一个男人走上台,拿着剪刀悬在小野洋子的头上,好像要捅她似的。而1965年在卡内基大厅参与活动的人显然更加狂热。在一段视频中,可以看到大多数男人急切地脱下小野洋子的衣服,包括一个花时间剪掉她的衬裙和胸罩带的男人。人群中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别这么讨厌!”而在整个过程中小野洋子坐在那里,双腿交叉放在一边,神色坚忍,除了她的眼睛偶尔会流露出焦虑和恐惧。当肩带被剪下后,小野洋子用手托起了胸罩。

小野洋子1964 年的行为艺术作品《切片》 图片来源:artchive
小野洋子曾将《切片》解释为一部关于脆弱、给予与和平的作品,但她很少像普林森塔尔那样给出女权主义的解释。“性侵犯是《切片》的表达,”普林斯塔尔认为,“性是其中不可否认的问题,但无论是小野洋子还是她早期的批评者,都没有把它作为性侵犯的一种表达。”一些当代的解读认为,《切片》是对原子弹事件后日本的象征,但并不能否认其中对女性实施暴力的可怕行径。弗里德援引一位评论家的看法:“真的很可怕——更像是强奸而不是艺术表演。”
几年之后,小野洋子创作的作品其实更符合这一看法。1968年,一篇名为《强奸》(或追逐)的文章描述了一种“用相机进行的强奸”:一名摄影师被要求跟踪一个在街上被发现的毫无防备的对象,“直到她进入某种状态。”第二年,小野洋子和约翰·列侬为《强奸》制定了剧本。在这部电影中,两名带着摄像机的男子在伦敦跟踪一名陌生女子长达一个多小时,先是在外面,然后进入了她的公寓。一开始,这名女子似乎很享受这种关注,但到最后,她却因为无法逃脱或得到帮助而感到恐惧和歇斯底里。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电影的观看体验相当折磨人。
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强奸》是一件罕见的作品,其中让一个女人充当了侵略者(虽然小野洋子没有出现在拍摄现场,但场景是她定的,摄像机是按照她的指示拍摄的)。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女性艺术家利用新的行为艺术类型来体现和处理她们作为受害者的角色——无论是公开的暴力还是更微妙的性别歧视。她们中的许多人是通过自残来达到目的的,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复杂了。而其中最极端的例子是玛莉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的《韵律》系列行为艺术:一个更复杂版本的《切片》,阿布拉莫维奇将自己麻醉后开始静坐,由观众挑选72件物件来接触她的身体,甚至包括一把上了膛的手枪,而她不作抵抗。
阿布拉莫维奇把自己推向极限,以看到自己可以忍受多少痛苦。相比之下,对于现场的暴力,古巴裔美国艺术家安娜·蒙特富尔(Ana Mendieta)则对暴力的情感更感兴趣,她会用自己的身体来制造暴力的效果。蒙特富尔的“血腥早期”(普林森塔尔如此称呼)是由爱荷华大学一名学生被强奸和谋杀的事件引发的,蒙特富尔当时在爱荷华大学读研究生。1973年,在谋杀案发生后不久,蒙特富尔邀请同学和教授到她的公寓。他们到达的时候发现门开着,艺术家在里面:她弯着腰,被绑在桌子上,内衣在脚踝处,腿上有血,头朝下倒在血泊中,破碎的陶器碎片散落在地板上。“鲜血淋漓的细节重现了那些最近在媒体上报道过的东西,”普林斯塔尔写道,“但你可以想象,蒙特富尔的同事们像入侵者一样进入黑暗、寂静的公寓,对所发现的一切毫无准备。弗里德记述道,他们坐下来讨论了这次的行为艺术,而蒙特富尔仍坚持了一个小时。

安娜·蒙特富尔未命名自拍
在这部名为《强奸现场》(Rape Scene)的作品之后,蒙特富尔又针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几次行为艺术。在作品《死在街上》(Clinton Piece, Dead on Street)中,她晚上躺在路上的血泊中,让一个同学用闪光灯相机给她拍照。在另一部作品《血色床垫》(Bloody Mattresses)中,她在一座废弃的农舍里铺满了破床垫、衣服、纸张和其他物品,墙上涂满了血红色的油漆(普林斯塔尔说,雕刻家查尔斯·雷曾偶然发现这座建筑,以为这里是真实的犯罪现场)。在另一部作品《强奸》(Rape)中,蒙特富尔又一次躺在木门外,满身是血,腰部以下全部赤裸裸。
蒙特富尔的行为艺术相当骇人,但并不盛大。她会刻意避免制造或再现暴力行为,而是迫使观众直面其后果,就像《洗礼》一样。她还会把自己的作品放在镜头前,很少有人看到现场的行为艺术。通过这种方式,她用自己的身体架起了行为艺术和更传统的二维艺术之间的桥梁。
蒙特富尔称《强奸现场》是“对暴力侵害女性的一种反抗”,她还表示,“我看不出在这种问题上有什么理论性。” 确实,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蒙特富尔和小野洋子,其他许多同期艺术家的行为艺术作品表达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暴力,以一种私密、个人的方式体现出来的暴力。这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强奸危机运动(rape-crisis movement)的发展,该运动始于女性在女权活动上分享自己的经历。只有当人们开始意识到问题的普遍性和系统性,有人公开自己的经历,形成一种集体性的证词,才能促进政治行动往好的一面发展。
行为艺术也遵循了类似的轨迹。在苏珊妮·莱西职业生涯的早期,她努力将个人生活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是艺术创作,她认为这是一种更个人化的努力;二是“观察这种政治活动背后的结构,并将其作为艺术作品的模型,这个看似简单的解决方案,直到行为艺术的新思想背景出现,我才想到”。她后来回忆道,“我想提供一个大众层面的对话结构,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意识。”
1977年,莱西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在那一年的5月7日到24日,莱西策划了《五月的三周》,包括一系列的表演和节目编排,以及一次前所未有的合作活动,这次活动就这样在艺术展的掩护下开始了。艺术展的核心是两张25英尺长的黄色洛杉矶地图,铺在市政厅下面的林荫道里。而当时,洛杉矶是美国的“强奸之都”。在这个项目进行的过程中,莱西每天都会收集警方的犯罪报告,并在其中一张地图上盖上红色的“强奸”印记。她会在每一个印记周围加上9个较浅的印记,代表未报告强奸案的估计数字。“随着记录在案的事件开始占据地图上越来越多的空间,公众的日常生活中开始出现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 弗里德写道。第二张地图则包含了支持受害者的信息,包括危险的方位、急诊室的位置和强奸热线。

《五月的三周》 图片来源:suzannelacy
这场为期三周的行为艺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美国艺术家莱斯利·拉博维兹(Leslie Labowitz)组织了四场抗议表演,莱西则在周末创作了一件更私密、更接近《洗礼》的作品。他们的行动有艺术仪式、示威游行、与洛杉矶副市长的新闻发布会,以及教堂的默哀。莱西将政府官员、女权活动人士、女艺术家和媒体聚集在一起,与市检察官、洛杉矶警察局、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以及“反对暴力侵犯女性组织”(Women Against Violence Against Women)和“男性反对强奸组织”(Men Against Rape)等组织合作。在这个过程中,莱西把行为艺术和行动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这也成为了她艺术生涯的基础——社会实践。
《五月的三周》以公众的日常生活为背景,因为莱西想要接触到比画廊里更多的观众,她也真的做到了。普林森塔尔解释说,“莱西和她的合作者们所展示的很多东西……对公众来说都是新闻。” 不过她补充说,这种影响并不完全是积极的,这个项目“似乎助长了反女权主义的反弹” ,包括一个女人在距离地图100码的距离被强奸。
尽管《五月的三周》这一行为艺术的规模比之前的性暴力表演要大得多,但它们的目标是相同的,那就是让人们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强奸问题。这些艺术家创造的是一些在美国文化中从未被公开讨论过——更不用说被看到了——的东西。他们坚持谈论禁忌话题,似乎很有先见之明地减少了这一话题的耻辱感,如今,几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对性侵犯的指控。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行为艺术采取了一个新的流派来开启关于强奸的对话。行为艺术提供了一种直接的、转瞬即逝的、难以理解的形式,它允许情感交流、实验性和激进冒险中的错误。它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空间,艺术家和其他人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言,并让观众成为创伤的目击者。弗里德甚至看到了更深层次的联系,她引用了学者佩吉·费伦(Peggy Phelan)和索菲·安妮·奥利弗(Sophie Anne Oliver)的话,她们认为,由于表演的短暂性,“表演”永远是对失去的演绎,是对不可能挽回的过去的演绎。表演可以模拟性创伤的情况和影响,但也可能有助于治愈它。
更重要的是,这种新的艺术流派带来了一种更抽象、更纯净的艺术语言的可能性。西方的艺术标准主要由绘画和其他图像艺术构成,女权主义作家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其1975年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违背意愿:男人、女人及强奸》(Against Our Will: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中所称的“英勇的强奸”:在神话和历史场景中,男性对女性的性侵犯被认为是维持文明秩序的方式之一。大多数这样的作品都是由男人创作的,普林森塔尔写道,对他们来说,艺术中的强奸主题往往是“寓意或隐喻性的”,但却几乎从来没有“对受害者产生影响的体验”。如果用绘画或其他二维艺术在70年代描绘强奸一定是个艰巨的任务,因为这也意味着要通过或反对之前的种种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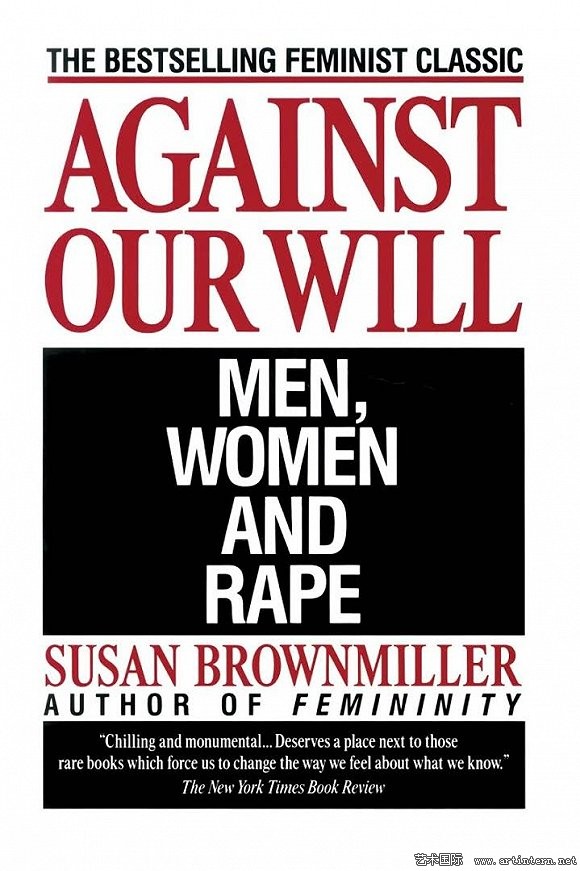
《违背意愿:男人、女人及强奸》
而一旦行为艺术和女权主义运动一起打破沉默,开始以性侵受害者为中心,这种文化就开始发生转变。最初的紧迫感——我们现在需要以某种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意识——让位于各种媒体之间更广泛、持续的对话,包括书籍、电视、绘画和照片。当代艺术在很多方面都处于这种对话的边缘,它很少能像政治运动或抗议活动那样,以同样的声音展现出来。然而,它所能做的是更新或重新集中我们的注意力。
2014年,美国艺术家艾玛·苏考维茨(Emma Sulkowicz)就做出了类似的行为艺术,当时她在哥伦比亚大学随身携带床垫,以抗议学校里强奸嫌犯的持续存在,以及校园里的性侵犯。类似的还有露兹妮·霍尔(Luzene Hill)的《反追踪》(Retracing the Trace),她花了60多个小时悬挂了近4000个由红绳做成的印加奇普绳结,以及奈马·拉莫斯·查普曼(Naima Ramos-Chapman)2016年的超现实古怪短片《无事发生》( And Nothing Happened),讲述了明星如何处理强奸造成的心理创伤。
在很大程度上,如今的艺术家会比他们的前辈们更加细致地处理性暴力。普林森塔尔写道,早期行为艺术中表达的是“近乎无言的恐惧”,后来的许多行为艺术作品则采用了更加广泛的基调,并倾向于将性暴力视为一个与种族主义、战争、媒体和流行文化等其他问题相交叉的问题,它可能只是一个更大故事中的一个片段。然而,很难估算这些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女性艺术家,以及之后的几代人(关于这几代人,目前还没有综合性的书籍问世)。虽然他们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但这些艺术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标准,并为性暴力艺术建立了一种新的视觉语言。50年过去了,我们仍在为它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