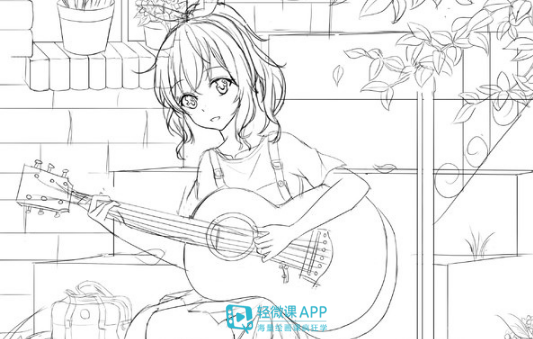特纳奖新得主:北爱尔兰“阵列团体”,把展厅变成“酒吧”
当地时间12月1日晚,2021年特纳奖颁奖典礼在英国考文垂举行,来自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阵列团体”(Array Collective)成为今年的特纳奖得主,这也是该奖项自1984年创立以来首次由来自北爱尔兰的艺术家获得。阵列团体将美术馆传统的白盒子空间变成了北爱尔兰式的酒吧,与此同时,其他四个入围艺术小组也均以社会参与和行动为特色,他们的呈现也区别于传统的展陈。这使围绕特纳奖的讨论不断“发酵”:或许,这些作品压根不该在美术馆里展出,而应该出现在艺术家们真正归属的社群里?

阵列团体(Array Collective)的现场展示 David Levene, courtesy The Turner Prize
阵列团体将获得2.5万英镑的奖金。另外四组被提名的艺术家团体也将被授予1万英镑的奖金。这是特纳奖首次只有激进艺术家团体入选,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单独参与。颁奖典礼在考文垂座堂(Coventry Cathedral)举行,这是一座被毁坏的哥特式教堂,如今只剩下空壳。81年前,1940年11月14日,德军在考文垂进行闪电战,被记录为二战中最具毁灭性的轰炸袭击之一。
这几个团体的作品正在考文垂赫伯特美术馆展出。奖项的委员会包括英国伦敦非营利基金会Delfina Foundation的总监Aaron Cezar、伯明翰画廊与艺术家工作室综合体Grand Union的项目总监Kim McAleese、演员兼藏家Russell Tovey,以及伦敦画廊Chisenhale Gallery总监 Zoe Whitley。泰特美术馆馆长Alex Farquharson担任评委会主席。
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展览的主策展人 Hammad Nasar赞赏了展出的作品,称它们具有“在现实世界中进行实践”的能力。
“参展的艺术家不满足于留意世界上的事物,然后通过博物馆和画廊里的作品向我们指出它们,”Nasar说道,“相反,他们致力于构建‘口袋乌托邦’(pocket utopia)——在现实世界中运用艺术想象力,提出新的、更平等、更有希望的未来。”

阵列团体
阵列团体从2016年起开始合作,他们的动机源于对北爱尔兰等地的“人权问题感到日益增长的愤怒”。成员们表示,团体的成立旨在“重新审视北爱尔兰有关宗教—民族认同的主流观念”。
评委会将奖项授予阵列团体,称赞他们“能够将他们的行动主义和价值观转化为美术馆环境,创造出受欢迎的、沉浸式的、令人惊讶的展览。”
在展览中,阵列团体将考文垂美术馆传统的白盒子展厅改造成了一个非官方的爱尔兰酒吧——síbín,或称“未经许可的酒吧”,这种酒吧起源于17世纪初的爱尔兰。但是这个团体表示,他们的作品是“一个让人在宗派分歧之外聚集的地方。”
我们通过旗杆围成的圆圈走进síbín,这个构造参照了古代爱尔兰的仪式场所。在内部,síbín放慢了人们通常不会在贝尔法斯特酒吧里找到的各种装备。由阵列团体创作的海报装饰着内墙,旗帜悬挂在天花板上。即使是那里的啤酒也有自己先锋的地方。
在这个灯光昏暗的小酒吧里,一段视频里播放着一个充满表演和愉悦性的夜晚,这样的夜徐徐展开。贝尔法斯特人们聚在一起喝酒聚会;他们一个个走上舞台,竞逐“天后歌手”的名称。其中有些是变装皇后,有些穿着极简的T恤和牛仔裤。人们唱歌,讲故事,表演单口相声。每个表演者都受到同样的欲望的驱使,让贝尔法斯特放下自己的过去,让人们聚在一起。墙上有一张粉红色海报,描绘了一个穿着高跟鞋坐在轮椅里的女人,“所有人都需要堕胎权,”她在会话框里“说道”。一面旗帜上缝着单词“废除”(REPEAL)。
今年特纳奖的候选者还包括烹饪小队(Cooking Sections),这个来自伦敦的双人组在苏格兰斯凯岛(Isle of Skye)展开大量工作,并于今年夏天在泰特现代美术馆展出了自己的作品。他们的出现让苏格兰捕鱼业头疼不已。

烹饪小队(Cooking Sections)的现场展示 David Levene, courtesy The Turner Prize
通过将渔场的圆形投影置于地上,烹饪小队关注密集的大马哈鱼捕捞,对于养殖鱼类的基因改造,在令人不安的声音中向我们讲述其背后的罪恶——即“人类是大马哈鱼无法逃脱的病毒。”烹饪小队积极地向英国各个城市的美术馆呼吁将大马哈鱼移出他们的餐厅菜单,并且达到了显著成效,蛇形画廊与泰特美术馆已经签名加入。
此外,候选者还有来自伦敦的“黑曜石音响系统小组”(Black Obsidian Sound System,简称B.O.S.S.),这个小组由黑人及有色人种同性恋、跨性别者等组成,他们于2018年夏聚集在一起,为了“延续音响系统文化的遗产”,反映了边缘群体如何创造出聚集的方式,来抵抗压迫。在特纳奖的展览中,小组的展示“将扬声器视为创造神圣空间的图腾。”在其展厅的中央,水池位于大型的扬声器上面,随着音乐的声音而振动,这些水面上的图案就像B.O.S.S.小组在一些特别的艺术空间里组织声音活动时,随之而聚集起来的人们一样。

B.O.S.S.的现场展示 David Levene, courtesy The Turner Prize
最成功的展示或许属于来自黑斯廷斯的Project Art Works小组。他们的展览主要展出了由神经多样性的艺术家们创作的绘画作品,这些有精神健康困扰、自闭症、学习及其他智力障碍的人呈现了深刻的内心感受。其中一些作品非常动人。但是其中很多作品被一起堆叠在展厅中间,而无法看清,这或许说明了这样的艺术一直都没有被更广泛的世界所正确对待。

Project Art Works的现场展示 David Levene, courtesy The Turner Prize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温和/激进”(Gentle/Radical),这是卡迪夫(Cardiff)河滨地区的一个社群项目,成立于2017年。这个囊括了社工在内的团体有着广阔而分散的雄心;他们举办活动,从电影放映到表演,再到“草根座谈会”,希望邀请卡迪夫社群各行各业的参与,将艺术视为一种交流和辩论的方式。他们的想法通过影像作品进行展示,人们在影像中朗读探索个人经历的信件。这样的想法值得称赞,但是与美术馆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且难以很好地传递出来。但这也正是问题的关键。

Gentle/Radical的现场展示 David Levene, courtesy The Turner Prize
特纳奖曾经被认为是单个艺术家殊荣,是一代英国艺术家就此开始享誉全球的主流平台。如今,评委会清楚地传达了他们的信息:个人的艺术是过去式。集体的艺术才属于当下。放在一起看,这些作品标志了特纳奖不断变化的身份,或许也代表了艺术在现代英国所扮演的角色的变化。这场特纳奖展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美术馆和画廊还是原来那样吗?又或许我们应该进行更深刻的观察?
另一方面,将奖项授予基金艺术家的决定也激起了分歧。批评者指出,奖项将当代自由政治的霸权置于好奇心或话语之上。他们指出,这种社会行动家式的艺术是单维度的,它毫无疑问地肯定了不言自明的真理——即现状是坏的,应该变得更好,我们都必须为此付出更多努力。这些显而易见的道理无法构成一场包容而激动人心的展览。也有一些人认为,特纳奖的转变反映了它自己的真相;即许多近期的艺术作品与当下现状没有太大关系,大部分内容仍然是对于一个世纪前的艺术家们在内容、理念、形式和风格上的复现,而且还比他们要逊色。艺术变得商品化,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与财富和精英主义达成一致,以至于几乎失去了除了基本装饰之外的所有目的。
对于支持者而言,特纳奖对于创造一种新的艺术愿景加以称赞,这种去中心的、平等的形式是有意义的。脱离了自省、自我与自恋的艺术能够帮助我们思考甚至克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2015年特纳奖得主Assembly Assembly
特纳奖的创立初衷是表彰一位在英国出生、生活或工作的艺术家,赞声其过去一年中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举行的出色展览或作品的公开呈现。这一切从2015年开始发生变化:伦敦社会团体Assemble成为首个获得特纳奖的小组。过去两年中,这一变化加剧了:连续两年的获奖者都不是单人艺术家。
今年的赢家已经揭晓。但辩论仍在继续:特纳奖的入选作品就得在美术馆空间里展出吗?是否可以在艺术家们真正归属的社群中呈现呢?
(本文编译自《The Art Newspaper》,有部分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