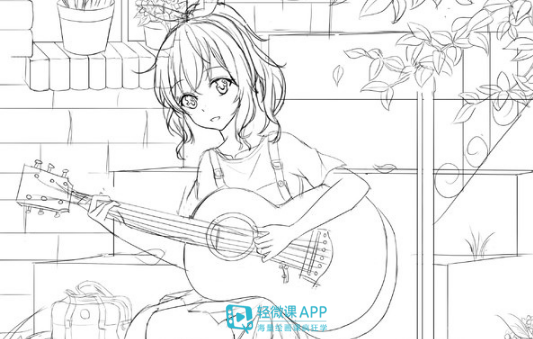王璜生:溯源记忆深处,致意珠江与广州

《西江船影》纸基银盐 王璜生1984年拍摄 2020年冲印

《源头·活水》展出现场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张 雯
图/受访者提供
1月22日,《出发与回归:致意珠江与广州——王璜生珠江溯源记巡回展》在广州图书馆拉开帷幕。
这是一场关于时空的对话,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总馆长王璜生以大量生动的写生、摄影、速写、写作文本作品,回顾珠江沿岸的民俗风物及上世纪80年代青年艺术家的精神风貌。
与上世纪的自我隔空对望
近年来,王璜生发起了一系列展览和创作,回望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冒险”经历,从桂林、昆明、贵阳,最后一站回到广州。
巡展缘起于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当时,王璜生找出了自己塞在抽屉角落里36年的珠江溯源日记本翻读,这段本被遗落的经历才被重新挖掘出来。
他将当时九万多字的日记、数十卷未冲洗的黑白胶卷以及大量写生画稿一起整理成书,出版了《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并由此书脱胎出“珠江溯源”巡回展览。
1984年,艺术家王璜生与挚友李毅结伴骑行,行程三千多公里,辗转粤桂滇黔四省,去追溯珠江的源。在这段翻高山、过谷底、走荒坡、宿野店的旅途中,王璜生及其同伴以理想主义的激情,热烈回应了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背景下,一代青年人对自我、对生活、对生命的追寻。
这次展览展出了艺术家1984年珠江溯源的部分写生、摄影、速写、写作文本等,以及重新创作的《珠江源植物图志》《远方与河》《骑走》《源头·活水》《远方与路》等新近作品。艺术家用一次巡回展览,与1984年时的自己隔空相望。
上世纪80年代,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在新潮艺术上似乎还未拔得头筹,那时的“小城文青”王璜生还在汕头“折腾”他的青年美协,又以“游学”的方式拓展视野、广结友朋,也积极寻求艺术上的变化。
策展人胡斌认为,“骑行”这一既根植于区域又带有强烈个体性的历险行动,在年轻的王璜生那里烙下了深刻印迹,为他后来掀起一个个由地方到全国的艺术行动埋下了伏笔。
珠江文化精神延绵不绝
巡展最后一站设在广东广州,除了是对珠江文明的一种呼应与回归,也象征着艺术家对故乡的深厚情谊。这里不仅是珠江流入大海的终点,也是王璜生开启艺术工作的第二故乡。
广州这座南方城市铭刻着王璜生的成长血脉,亦见证了他多年来在人生态度中对理想事业所抱有的初心与热望,对他而言至关重要。
在广州站的展览作品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源头·活水》,这是艺术家新创作的综合材料装置作品。王璜生的诠释是,唤起我们对从涓涓细流到汹涌澎湃的珠江水能量的遐想。
“珠江”既是一种地理上的流域概念,也是在文化层面关于时代与空间的描述。策展人孙晓枫认为:“‘珠江’在近代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性的、充满实验精神与革创力的名称,从源头到流域的文化,共同塑造了珠江的历史、思想和性格,并为珠江注入了文化特质与活力。王璜生珠江溯源的个人意义,则体现在对一种兼容、饱满、开拓的人格塑造。”
重走当年路,体会到的“变与不变”让王璜生印象深刻。当年他们在广西燕来的山村见证村民们极富仪式感的习俗“立房子”,前年回到那里,这个村子已经进行了迁移,变成天生桥水电站的一部分;贵州的一座小城里,当年他在一家小书店居然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而在三十年后,这家小书店虽然已经几易其手,但依然存在,“这或许是珠江文化精神延绵不绝的一点体现吧。”
访谈
通过办展览“倒逼”出新的创作
羊城晚报:这个系列展览每到一站都有新的作品展出,您是怎么考虑的?
王璜生:对,做展览其实在倒逼着我创作新作品。从第一站桂林开始,我就想,每一站都要有新的创作,要跟当地的文化发生关联。当年在桂林,从珠江源头采集了不少植物标本,现在的新作品是回到源头再去采集并作延伸。
第二站昆明,展览空间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就将原来的植物再转换成影像,并融入了上世纪80年代对我们思想影响最深的东西,比如当时的朦胧诗。在这个过程中,也尝试加入了新的形式、材料和手段,比如喷枪喷绘等。
第三站到贵州,让我想起了当时艰难的骑行经历,就用28寸的大自行车在宣纸上骑行并留下水墨的痕迹,进而有了作品《骑走》。出来以后反响还不错,它跟水墨、溯源、行动有关,同时拍摄了一点影像,体量也更大。
羊城晚报:到了这次广州巡展,却有两件新作品。
王璜生:巡展最后一站设在广东,也是我对过去那段经历的一种回应。从一开始,我就希望作品能呈现珠江的一头一尾。我自小生活在海边,小时候经常玩浮石,它是由海浪的泡沫跟沙土所形成的石头,能在海上漂,我觉得挺有意思。后来我查阅资料,得知在珠江的出海口,万山群岛中的万山岛有一个浮石湾,它在烟雾缭绕之下,像浮起来一样,堪称奇观。于是我希望能够用珠江源头的水将石头浮起来,这寓意着珠江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流淌,从涓涓细流到汹涌澎湃,最终流入大海,能将石头激荡到浮出水面,这是多么大的力量!
另一件作品的创意是我想用源头的水,滋养珠江下游的植物——比如榕树叶,以突出珠江作为生命之源的意象。
羊城晚报:当时出发溯源的考虑是怎样的?近年梳理这段经历有怎样的感受?
王璜生: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偶然的,比如我和朋友出发溯源珠江,当时并没有想什么远大的目标,只是觉得好玩。很多人都走过长江、黄河,我们就想走一条“小路”——相对少人走的珠江。那段经历过去后,我回到汕头,而后又去了南京、广州、北京,再回到广州,当时留存的东西都一直放着、没有再管了。
2020年疫情发生的时候,我才有空整理了一下旧物,重新看到当时的文字和作品,都深受触动:在那么艰难的路途上,年轻的我一直坚持着,坚持走路、坚持画画、坚持写作。我重新感受那个年代中的自己,体会那个特定时期的理想、审美以及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现在看来虽然有些稚嫩,但也很有时代特点。
不过,如果只是回顾就没多大意思了。我就借这次梳理的机会,重新做了一些作品,尝试超越过去的创作,不同于我之前那些“铁丝网、线条以及伤害的主题”。我从某段历史出发来结合当下,也能更好地激发自己应用新的艺术方式,挑战自我。
感受珠江的乐观、愉快、阳光、有力量
羊城晚报:这一段溯源经历给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王璜生:三十多年过去了,一路走过来,正是过去的点点滴滴汇成了现在的我。这段骑行影响到了我后来对待社会、对待个人、对待工作的方式,无论是我在广东美术馆,还是其他美术馆,都希望自己有一份坚守甚至独立,这跟当年那种不辞万难、努力达到目标的劲头是相关的。
羊城晚报:那您如何评价50后60后艺术家的特点?
王璜生:与新生代相比,50后、60后艺术家经过了一个封闭、压抑的历史阶段,个人经历让他们有强烈的意愿去了解外部世界、冲破一些限制。当然这也是必须的。这份冲动和愿景塑造了他们对自身文化的批判和审视态度,令他们的作品更具有力度。
由此,这一代的艺术风格构成了重要的历史现象。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特质成为了他们内在的、本质性的特点,同时也可能延续这种态度去对待新时代的艺术。这个过程相对复杂,也构成了艺术当下的一种丰富性。
羊城晚报:珠江流域有什么样的文化特征?
王璜生:在我们看来,珠江充满野性和活力,无论江水和植被都有着“生猛”的生命力,有着乐观的精神和向上的力量。这恰恰是珠江流域的人文特征所在,是关于珠江文化为何“开风气之先”的最好说明。
珠江固然和长江、黄河大有不同,而珠江流域这么广大,如果要谈它一个最重要的特点,要从地理、生态来讲。
我感触最深的是,珠江的水流量仅次于长江,中国排第二。而且它的流水落差很大,给各个地区都带来了丰厚的资源、能量。整个珠江流域水源充沛,气候宜人,从源头到出海口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这也孕育了广东乃至珠江流域的这种生态以及人文特征:乐观、愉快、阳光、有力量。
这次展览组织邀请了一些青年学者和艺术家参加讨论,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来自西南地区,对珠江上游进行带有行动力的表述,我也会用类似的行动或者观念、材料等接着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