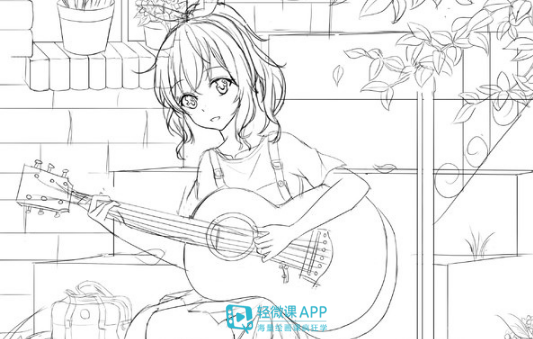考古水墨作品创作随笔——《双联同心》与一件出土文物的故事

双联同心(中国画)赵曼
作为一个执毛笔为生的画家,用大量的时间、精力研究出土文物和考古学,似乎有点跨界太远,但将考古与水墨融合进行创作,却成了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
在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些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这些陶器在今天的人看来不足为奇,但在5000多年前,在那个一切都要向大自然求取的时代却显得弥足珍贵。仰韶文化源自火与土,更源自华夏先民从完全受自然支配进入到通过种植培育粮食自给自足的时代。他们烧制陶器,储存食物,积累更多财富;营建村庄,形成氏族、部落。
近些年来,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彩陶类型有了越来越细的划分,总体而言以实用器为主。用于家族聚餐使用的大型盆、罐非常常见,唯独有一个彩陶双连壶,小巧朴素。这个彩陶双连壶由两个类似于现代温酒壶大小的小壶连接而成,简单的横竖斜线装饰,似乎看不出它有多么不寻常,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壶,自20世纪70年代出土后却再未发掘出与它同一类型的器物。而在它出土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郑州市博物馆组织的考古发掘队也并未发现这是两个可以连接在一起的壶,直到考古学家严文明经过比对其碎片的造型才发现这是一个可以合体的器物。
尽管彩陶双连壶在考古学界有其独一无二的特殊性,但也仅仅是作为文物陈列在博物馆。多年来,和大多数参观博物馆的游客一样,我并不记得它的存在,但当我开始了考古水墨创作后,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器物。前后绵延迭代长达3300年的郑州大河村遗址既发现有仰韶文化类型彩陶,也发现有东夷大汶口文化彩陶,这说明在5300多年前,山东泰安与河南郑州的远古邦国之间已经有了往来,两大集团的联盟或战争,很有可能促进了彼此文明的发展,而双连壶,无论是它的独特性,还是它身上抽象线条可能隐含的图腾意义,或是考古学家对其可能用途的推测,无不暗示着这也许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实用器。然而年代久远,又没有文字记录,无论怎样都不可能还原它在那个时代的真实作用,但如果想让这件文物具有与其独特价值匹配的文化意义,那在创作中,就应该赋予其画眼的位置。
于是我以“部落联盟”的构思进行了第一次创作,但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如果两位男性首领共执此壶,歃血为盟,则需有配套的双连杯,否则无法从壶中倒出酒以完成仪式,而相应的出土文物中也并没有小酒杯这种器物供参考。并且,由于壶体过于小巧,与庄严的结盟现场和洪荒时代的大背景显得格格不入,经过两次尝试,最终我放弃了这一思路。我再次驱车来到大河村遗址,我熟悉这里的展厅,熟悉文献资料上许多陶器的介绍,但这些都远远不够,我需要让自己的整个身心在这里回归远古。
触摸着脚下的土地,它们曾经在数百年前可能是黄河上游沿岸的沙土和泥浆中,随着不断改道泛滥的黄河波涛席卷而下,层层堆积。在5000多年的时光中,这些泥沙掩埋了大河村遗址,而在这遗址之上,又有一代代劳动者不断耕耘、收获,直到考古学家将它们发掘出来,我们才能如此直观地看到历史与当下在同一片土地上重合。
温饱,曾经是这片土地上多少代人们的梦想啊!为了生存,人们需要集体的力量;为了让后代活下去,人们需要稳定的家族关系。如此可以想见,黄帝取妻嫘祖,之于世族联盟转化为国家形式,必然有着非凡的意义。作为一件象征通过婚姻而形成部落联盟的信物,这件有可能随着首领远征四方的彩陶双连壶该如何携带?壶身两侧可穿绳的环突,给了我创作想象的空间。一条绳子,连接的是两个人的心,也是两个部落的盟约,由此,画面的核心部分便是由新郎执壶,新娘穿绳子,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展开。
围绕着中心人物,我在这一对新人旁边增加了手执大汶口文化灰陶鬲的中年男子,及几名手持大河村遗址出土陶鼎、陶罐的男女老少人物形象,又将那个时期可能出现的狩猎麋鹿、羊、驯化的猪、打渔的人物形象填充到画面里,尽可能地还原洪荒时代人们所拥有的财富。
在创作中,我坚持规避连环画式的图文解说形式,尽可能地把我在遗址现场体会到的远古气息用水墨写意加以表现。我希望人们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能感受到这一件出土文物在5000多年前被我们的先民使用,在这漫长的时光中,它和许多陶器一样沉睡在泥沙之间,就如同我们许多人,在不如意的阶段仿佛被世界遗忘,但只要存在过,就会留有痕迹,只要留有痕迹,就值得被纪念与尊重。我们尊重历史、缅怀先民,就是在追寻我们的血脉来自何方;当我们从这世界消失,留下的并不是虚无,而是曾经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存在于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