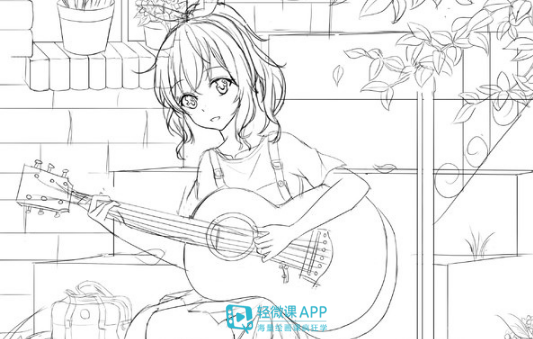韩琦请欧阳修写“评论”


北宋很多名臣权相、文人富绅,只要有点钱,都喜欢修宅院。有些是自己享乐,有些则是比阔。像晏殊、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人,都在汴京和洛阳有豪华的私家园林。然而,虽然他们心中十分满意,也颇为自豪,但几乎都不敢公开炫耀。因为越是繁华,越是说明他们搜刮了民脂民膏。正因为这样,当宰相杜衍退休后,住在只有10间房的宅子里,其简朴从容便赢得了很多人的尊敬。
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修了大宅院或亭子后,特别喜欢“广而告之”,不仅请名人写文章,还要请著名书法家书写刻石。这方面的例子最有名的当属范仲淹为滕子京写的《岳阳楼记》,与之不相伯仲的,则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稍次则是欧阳修为韩琦撰写的《昼锦堂记》。
这些在庆历新政前后被“弄下去”的人,在各自偏陋之邦大修园亭,为什么还要大张旗鼓、生怕别人不知道?就不怕被政敌收拾吗?是的,他们就是想让政敌知道,更希望皇帝能看到。
比如韩琦的昼锦堂。
相州是韩琦的家乡,48岁的他从宋辽边境的并州调回相州后,便将衙署的后园改造成一座园林,园林中修筑了一座大堂,名为“昼锦堂”。
取名“昼锦堂”,听上去很嚣张。“昼锦堂”,自然是“锦衣夜行”的反语。穿着锦衣晚上出行,谁看得见?富贵还乡,当然得锦衣昼行。韩琦虽然此时只是相州知州,但他的头衔是“武康军节度使”,对于家乡人来讲,当然算得上是富贵还乡了。如此露骨,就不怕被人告发吗?
一年之后,园成,韩琦亲自撰写了《相州新修园池记》,时为至和三年(1056年)三月十五日。他在文章中写道:
既成,而遇寒食节。州之士女,无老幼,皆摩肩蹑武来游吾园。或遇乐而留,或择胜而饮,叹赏歌呼,至徘徊忘归。而知天子圣仁,致时之康。太守能宣布上恩,使我属有此一时之乐,则吾名园之意,为不诬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园林修好之后,正好赶上寒食节。相州的士人妇人,无论老幼,都来我的园林里游乐,游人摩肩接踵。有的人遇上好玩的,就逗留好久。有的人则找个好处所喝酒唱歌,大家流连忘返。从而知道天子的睿圣和仁德,让这个时代安康太平。我是相州知州,我将皇上的圣恩传递给这里的老百姓,让老百姓得享这些快乐,那我为这个园子取名为“昼锦堂”就不负初心了。
原来韩琦修这座园林是为了给当地老百姓游玩,而不是为个人享乐。他的“昼锦”之意也并不是显示自己的功名与富贵,而是宣扬皇恩。
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范仲淹为滕子京所写的《岳阳楼记》。当年滕子京与范仲淹、韩琦一起在西北抗击西夏,由于军费不够,他用走私所得的钱财补充军费,被反对派追查。要打垮像滕子京这样在西北领兵打过仗的人,从军费上查,一般是一查一个准,因为国家拨的军费都不够花,军队领导只能额外找钱。尹洙也因这事儿栽了。滕子京知道对不上账,所以在检察官获得“罪证”之前,将账本全烧了。滕子京毫无悬念地被贬。他在贬谪地岳州修建了一座大楼,名“岳阳楼”,请范仲淹写一篇记,其始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这样的开头,必须得结合宋夏战争以及庆历新政来理解,否则对“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理解不能到位。因为滕子京不仅是范仲淹的好朋友,更是他所认定的治国之能臣。范仲淹在改革中需要的就是这样能使偏远地区都能“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人才。
其尾曰: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这几句光耀千古的名言,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标杆。这样的结尾,使得文章的立意就与岳阳楼没有关系了。楼,只是一个符号,忧国忧民才是士大夫必备的本质。
当滕子京在岳州谪居时,欧阳修也正在偏陋的滁州任知州,“知州”相当于唐代的“太守”。欧阳修在政事之余就是饮酒作乐、写诗填词。他在那里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联系他一生的行迹和思想,这真不只是一篇文人的赏景游玩之作,而是家国情怀的另一种表现。当范仲淹在为贬谪的滕宗谅写下《岳阳楼记》,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欧阳修却已然在文章里描述了他的乐: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
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
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滕子京的岳阳楼,欧阳修的醉翁亭,韩琦的昼锦堂,都可以称得上是北宋士大夫勤政爱民的独特符号。
但韩琦在相州与民同乐的日子并不久。
相州位于汴京正北方约200公里处,韩琦能快速获知朝廷中发生的状况。在他写完《相州新修园池记》后4个月,也就是富弼、文彦博拜相后一个月,即至和三年(1056年)七月二十三日,48岁的韩琦回朝担任三司使,成为中央权力的第三把手。
二府三司重新回归到当年改革派的手中,然而,富弼、文彦博、欧阳修、韩琦4人相差不过4岁,政治权力的追逐还将继续。
欧阳修在开始时是富弼的坚强盟友,后来逐渐被韩琦争取过去了。韩琦担任三司使不到两个月,就联合欧阳修,把身居枢密使之位的狄青给参倒了,韩琦接任枢密使,成功上升至朝廷权力的第二把手。两年后,韩琦又挤掉文彦博,与富弼同为宰相,终于正式拜相。
韩琦仕进之路,就像他33岁那年领兵攻打西夏一样,从来都是进攻型,而非防御型的。联想到富弼在《温柑帖》中对蔡襄所说的“今天下文章,惟君谟与永叔主之,又生平最相知者”,可以感觉到韩琦在朝独相进发的征途中,彻底将富弼给孤立了。
就在富弼于洛阳守母丧期间,仁宗皇帝也已经快不行了,皇位继承人成了深宫和外廷最为关注的重大事件。仁宗皇帝没有儿子,于是将宗室濮王赵允让的儿子过继为儿子,改名赵曙。嘉祐八年(1063)农历三月二十九日,54岁的仁宗去世了。在韩琦的精心安排下,赵曙顺利登基,是为英宗。
英宗登基后的第二年,即治平二年(1065年),57岁的韩琦于百忙之中想起了10年前建造的昼锦堂。相比此时,当时的情形还真算不上衣锦还乡,毕竟当时的实权只在相州,哪能跟现在相比。现在才是真正的衣锦还乡,他可以光明正大地锦衣昼行。他把当年写的《相州新修园池记》拿给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看,请他为昼锦堂写一篇文章。欧阳修虽是疾病缠身,却是第二天就将文章交给了韩琦,名为《相州昼锦堂记》。文章以雄博的美言将韩琦盛赞了一番,韩琦读罢大喜,立即回复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琦再拜启:
信宿不奉仪色,共(恭)惟兴寝百顺。
琦前者辄以《昼锦堂记》容(按:《赵氏铁网珊瑚》中这里为“容”字)易上干,退而自谓,眇末之事,不当仰烦大笔,方夙夜愧悔,若无所处,而公遽以记文为示,雄词浚发,譬夫江(按:《赵氏铁网珊瑚》中这里为“江”字)河之决,奔腾放肆,势不可御。从而视者(按:《赵氏铁网珊瑚》中这里为“者”字)徒耸骇夺魄,焉能测其浅深哉!
但褒假太过,非愚不肖之所胜,遂传布之大,恐为公文(按:《赵氏铁网珊瑚》中这里阙“公文”二字,由此可知,这幅字有可能是伪品)之玷,此又捧读惭惧,而不能自安也。
其在感著,未易言悉,谨奉手启叙谢,不宣。
琦再拜启(阙)台坐。(按:《赵氏铁网珊瑚》中这里没有阙字,内容为“参政侍郎”四字)
这就是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的《信宿帖》。
韩琦可以说是在最恰当的时候请最合适的大文豪欧阳修写了《相州昼锦堂记》这篇能载入史册的、具有盖棺定论性质的个人评价文章。然后,他又请大书法家蔡襄誊抄了一遍。韩琦也是蔡襄的恩公,蔡襄当然也是愿效犬马之劳,于是在蔡襄的书迹中有了一份楷书书写的《相州昼锦堂记》。欧阳修也很开心,他说蔡襄一般不给别人写书法,但会经常书写他撰写的文章。
韩琦抱稳了英宗的大腿,富弼无拥立之功,两年后,富弼以病辞相,宰相韩琦与曾公亮权兼枢密院事,也就是东府的宰相一并把西府的权力也把持过来了,58岁的韩琦成为名符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不久,英宗病逝,韩琦又成功扶持了神宗登基。至此,韩琦是相三朝、立二帝,他和欧阳修算是功德圆满,地位再无人可以撼动。
神宗上台后的第4年,欧阳修以太子少师身份光荣退休,第二年安然病逝于颍州宅第,享年66岁。3年后,韩琦在老家相州寿终正寝,享年68岁。两人俱是衰荣无限。
(作者系北京画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