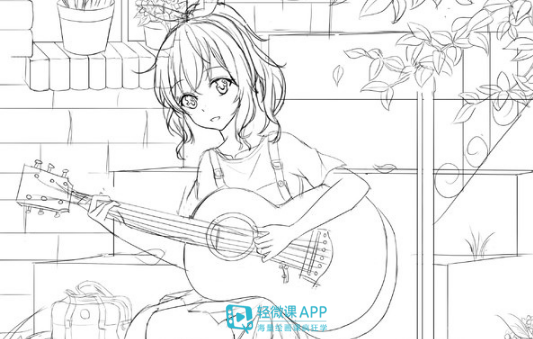在张岱的龙山下,举办戏墨展览

本文配图均为展览作品
主办单位
绍兴市文化馆
承办单位
张桂铭艺术馆
协办单位
青藤书画艺术研究院
展览时间
2021年9月展览地点
张桂铭艺术馆
绍兴市越城区仓桥直街41号
参展艺术家
王振尧、王逸、王怡新、王卫华、方本幼叶剑波、古雀、司马周、孙昊淳、吕雪峰阳帆、张斌、陆筱箐、吴邦羿、杨际一、林孝爽姚瑶、顾迎庆、清谷、龚纯皓、管辛、熊锦绣
(按姓氏笔画排名)

展览 · 剧场
文/徐显龙
许多年后,披发入山、俨然野人的张岱依然记得天启六年那一晚,龙山下了大雪,深三尺许。大雪晚霁,他带着家中伶人李岕生、高眉生、王畹生、马小卿、潘小妃,坐上城隍庙山门。看着“万山载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呆白”,生出无限的苍凉感。他们喝酒御寒,随后,马小卿唱曲,李岕生吹洞箫和之。雪地如同一个素白的剧场,主仆演绎着一段晚明最后的繁华(那一年,皇太极在沈阳登基,是为清太宗)。十八年后,明朝覆亡。
一
张岱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卒年约在1679年前后。张岱出身官宦之家,高、曾、祖三代皆为进士。在家庭熏陶下,他自幼聪慧,并爱好史学。由于当时家业殷实,生活优越,他兴趣广泛,喜游历,常盘桓于江南繁华之地,自云:“余少爱嬉游,名山恣探讨。”又好美食,坦言口腹之欲:“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日为口腹谋。”

王振尧 · 绍剧《三打白骨精》
此外,张岱还“好梨园”“好鼓吹”,自己会唱曲,善于创作剧本、赏评戏剧。从祖父辈开始,张岱家先后蓄养过六个戏班。私家堂会并不能满足他的戏瘾与玩心,当时还有各种形式的演出,令张岱着迷。在回忆录《陶庵梦忆》里,他如是记载——庙会。陶堰的严助庙,正月十五庙台前演出《荆钗记》《琵琶记》。颇为有意思的是,台下坐一老者,是群众指派的“监督员”。他眼睛看着剧本,耳朵听着台上唱,如果演员有一字脱落未唱,台下观众就会群起噪之,喝倒彩后戏班必须将所演之剧再从头开始。

王逸 · 百戏起源
野台。张岱的叔叔在空旷的地方“选徽州旌阳戏子,剽轻精悍、能相扑跌打者三四十人”,演了三天三夜的“目连戏”。到精彩处,万人齐声呐喊,竟传到府衙中,端坐着的熊太守乌纱帽一颤,以为是倭寇进犯。水台。一个叫包涵所的人在西湖上建造有大中小三号船,头号最大,优伶可以在船上为主人和宾客演戏;二号船载书画;最小的专供家中姬妾乘坐。凡有客人来,“歌童演剧,队舞鼓吹,莫不绝伦。”楼船游弋于西湖之上,停泊在雷峰塔或飞来峰下,许多人也驾着舟船追随着看演出。

王怡新 · 沧浪观月
不仅有以上这些实体剧场的演出,时人的生活也俨然是一个大剧场。某次求雨集会,人们为了凑齐“水浒人物”,甚至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在城里找不到,就到郊区、村子、山僻、邻府州县找,“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他们鱼贯而行,被围观者兜截遮拦,看个不停,俨然一场cosplay、浩大的“狂欢节游行”。就在这当口,做过京官的叔父张汝懋老人却责问张岱说,《水浒》和求雨有什么关系?近来山盗蜂起,你却把“梁山盗贼”迎来了。什么意思?张岱觉得还真是成了问题。但终究脑筋转得快,说,等三十六天罡星过后用皇帝特使宿太尉殿后,再打出六块牌子,两块写“奉旨招安”,一块写“风调雨顺”,一块写“盗息民安”,再有两块用更大的字体写“及时雨”,放在队伍前导行。这样一来,果然观者欢喜赞叹,老人“匿笑而去”。

方本幼 · 半掩柴扉
所谓求雨,大概也就是人们看戏的由头而已。
二
张岱戏曲生活的高光时刻,非“金山夜戏”莫属——崇祯二年中秋后一日,余道镇江往兖。日晡,至北固,舣舟江口。月光倒囊入水,江涛吞吐,露气吸之,噀天为白。余大惊喜。移舟过金山寺,已二鼓矣。经龙王堂,入大殿,皆漆静。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残雪。余呼小奚携戏具,盛张灯火大殿中,唱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锣鼓喧阗,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摋眼翳,翕然张口,呵欠与笑嚏俱至。徐定睛,视为何许人,以何事何时至,皆不敢问。剧完,将曙,解缆过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

叶剑波 · 七夕晒书
张岱带着戏班趁夜在镇江金山寺演出“韩世忠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惊醒了一寺的人起来观看。张岱导演即兴发挥,戏班从容配合,演员全情投入,以天地为舞台,以实景为配景,以夜幕为背幕,以月光来照明,以夜露为舞台烟雾,在历史现场对历史故事重新演绎,令寺僧瞠目结舌。在张岱麾下,调教的戏人不少。花旦“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性命于戏,下全力为之。”他交游彭天锡等艺人,对演员们熏陶。“天锡多扮丑净,千古之奸雄佞幸,经天锡之心肝而愈狠,借天锡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锡之口角而愈险。”

古雀 · 包公
此趟途经金山寺,他是带着戏班去兖州为父亲祝寿。后来,戏班在兖州演出张岱改编的《冰山记》,守道刘半舫看后,认为还少了几幕故事。张岱听说后,当天夜里就开始重新填词,并亲自监督小戏童强记新戏词。第二天到道署演出时,剧本已经增加到七出戏了。刘半舫对张岱的捷才十分惊异,于是与张岱结交。曙光渐渐照亮了金山寺的飞檐。待戏演毕,一行人迅速离开,山僧望着小舟在江面上渐行渐远,不知这群人“是人、是怪、是鬼”。

司马周 · 斌斌婕妤
张岱坐在船尾,看着金山在碧浪中越发渺小,而僧人们还兀自站在那里目送。张岱大闹一场,并迅速置身事外,忽然返身觉察着每一个人的反应,收获着无限的乐趣。现实生活多精彩啊,一个个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心思,不同的情状,在交错中进行着奇妙的化学反应,不也在演绎着一出出好戏吗?
三
张岱父亲曾经在鲁王府做事。南明时期,小鲁王朱以海流亡绍兴,驾临张岱宅第。张岱特意安排《卖油郎》一戏,演到“泥马渡康王”的情节,“与时事巧合,睿颜大喜”。

孙昊淳 · 曲倦灯残
“泥马渡康王”是一个传说。北宋末年,时为康王的赵构在逃难途中梦见神人告知金兵将至,猛然惊醒,见庙外已备有马匹,遂乘马狂奔。这匹马居然载着赵构渡过黄河的一条支流,过河后即化为泥塑之马。后来,赵构逃到南方,开启了“南宋”朝廷,宋祚得以延续,遂将越州改名绍兴(延续兴旺的意思)。显然,这暗合了南明小朝廷的境遇与期待。清兵大军压境,张宅里依然觥筹交错,他们享用着末世的荣华。未知的明天即将到来,在生活已经毫无指望的困境里,只得勉强沿着原先的轨迹继续滑行,无奈地等待着王朝更迭的宿命。彼时,画家陈洪绶也在座。鲁王还命陈洪绶画扇子。张岱说,陈洪绶画的《水浒》,个个栩栩如生,对着画喊出“宋江”、“吴用”,画里的人“无不应者”。张岱赞道:“(陈洪绶)以英雄忠义之气,郁郁芊芊,积于笔墨间也。”

吕雪峰 · 戏曲人物
但这一晚,陈洪绶不胜酒力,在御座边上吐了一地——人生总是充满谐谑,临到清军强迫剃发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陈洪绶索性一股脑儿剃个精光,装扮为僧,就像他笔下的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那样。
四
张岱选择披发藏于深山,过着“野人”般的生活。漏屋破窗下,十八年前龙山看雪的情景又回到了眼前——夜越来越深,气温渐渐低了,伶人的曲声箫声为寒威所慑,竟咽涩不得出。到了三更,一行人返家。马小卿、潘小妃两个女子相互抱着,从雪山旋滚而下,直至山趾,浴雪而立。而他,则坐一小羊头车,拖冰凌而归。

阳帆 · 牵牛织女渡河桥仙
张岱想起了金山寺演戏的那一晚清辉的月光,也想起了崇祯五年在湖心亭看雪的痴人对饮(那年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张岱泛舟到西湖湖心亭上,竟然遇到两位金陵人也来看雪,拉他喝酒聊天。下船后,舟子喃喃说道:“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但这些都没有龙山的那场雪在张岱的记忆中明晃,那是一位主人和几位优伶之间的日常状态,平常到几乎没有情节。这在他旧日漫长的享乐人生里连个插曲都算不上,顶多只是饭局上一笑而过的谈资,却恰恰成为了身遭世变后最可留恋处。人的一生会有多少波澜?如果没有清军南下,张岱恐怕会舒服到死。当若干年以后,他在石室竹瓦、破床碎几中度过晚年,再回望那一晚上,两个花旦在雪地里像花一样簌簌飘落的场景,犹如梦中,深感人生也是一个剧场。曾经的自己在里面蹦蹦跶跶,活得那么不真实。

张斌 · 归宋
龙山,又名越王山,勾践在这里卧薪尝胆,谋划灭吴。龙山,又名种山,勾践灭吴后,杀了功臣文种,葬于此处。龙山,本身就是一个剧场。戏中有戏,俄罗斯套娃一般繁复着。
五
张岱借着月光下抚摸曾祖父张元忭先生传下的棕竹扇子,心头沉重。这把扇子是沈梅冈先生在狱中制作的。先生因得罪严嵩,在狱十八年。读书之暇,旁攻匠艺,把一张铁片磨得锋利,削棕竹数片,做成这把扇子。如此气节,让沈先生对抗了时间的囚禁、桎梏的囹圄,终于获得精神的自由。曾祖父为这把扇子写铭:“塞外毡,饥可餐。狱中箑,尘莫干。前苏后沈,名班班。”将沈梅冈的节操与塞外牧羊的苏武并列。

陆筱箐 · 宝扇持来入禁宫
沈先生终于等到了严嵩伏诛,冤案昭雪。这固然可歌可泣,但“亡天下”的现实,显然比政治倾轧更让人椎心泣血。张岱也想过一了百了,身殉旧日的王朝、过往的文化。但曾经的经历令他夜不能寐,他的担当也不允许他有赴死的念头。除了沈梅冈的扇子,另一把扇子交替在梦里浮现,那是陈洪绶终究未在鲁王面前画下的空白扇子,像清冷的雪,在梦里发光,仿佛隐喻一个在大地上被抹得干干净净的王朝——那位在张岱宅第里豪饮的鲁王逃离绍兴后,在沿海居无定所,最终死于金门岛——别人没有见过的,他见过了;别人没有经历过的,他经历过了;别人没有思考过的,他思考过了。他恍然意识到自己有责任记录下来,他有了治史的冲动。他痴迷于戏,见一出好戏,恨不得“法锦包裹,传之不朽”——直接从舞台上热乎乎地“打包带走”,不仅自己享用,也供后世享用。他把好戏比作“天上一夜好月”,以及“得火候一杯好茶”,如果只可供一刻受用,实在太可惜了!

吴邦羿 · 佳期如梦
对戏如此,对亲眼所见的历史,更是如此。他想起了司马迁,以残破的身体为一个民族留下了记录三千年历程的《史记》。他决定编撰一部《石匮书》,要为大明王朝留一段信史——大戏落幕,应该把剧本整理记录下来。冥冥之中,他知道,自己俨然就是另一个司马迁——历史的剧本早已写好,身在其中的人,只是扮演一个预定的角色而已。
六
有研究资料说:“明末清初江南文士激烈抗清受到政府沉重压制和打击。清初文士剧刻本被销毁,文士蓄优伶也被禁止,文士层的戏曲活动因此严重萎缩甚至趋于消失。”

杨际一 · 龙山雪
“有那一条辫发拖在背后会有什么风雅,正如缠足的女人,我不相信会是美人。”民国年间,周作人在给重刊的《陶庵梦忆》作序时,写道:“我记起《梦忆》的一二则,对于绍兴实在不胜今昔之感。明朝人即使别无足取,他们的狂至少总是值得佩服的,这一种狂到现今就一点儿都不存留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的,绍兴的风水变了的缘故罢,本地所出的人才几乎限于师爷与钱店官这两种,专以苛细精干见长,那种豪放的气象已全然消灭,那种走遍天下找寻《水浒传》脚色的气魄已没有人能够了解,更不必说去实行了。他们的确已不是明朝的败家子,却变成了乡下的土财主,这不知到底是祸是福!”
七
看罢《陶庵梦忆》最后一页,像是过完了一生。

林孝爽·《陶庵梦忆》句
张岱留下的书,也像我们前世的一个梦。“城郭如故人民非”,周作人感慨。龙山脚下,如今有个看戏的新处所,绍兴大剧院。这幢模仿悉尼歌剧院的建筑里,为我们演出了《鉴水吟》《梁祝》《一钱太守》《陆游与唐婉》《王阳明》《青藤狂歌》《鉴湖风云》《祥林嫂》等本土大剧。这些故事,都发生在绍兴城里。小城本身就是一个大剧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大地却永远长存。”(《圣经》)如今疫情反复,演出一次次改期,一次次停演。恍惚间,一个平静的时代也在我们眼前戛然而止。

姚瑶 · 功夫
一柄折扇、一团宫扇,在才子佳人手中,总是能演绎出无限风情。它是戏曲人物的另一张面孔,荡漾开表情,闪现出眉目(昆曲有“文扇胸,武扇腰,丑扇肚,媒扇肩,僧扇手心,道扇袖”的说法)。今天,书画家们在扇面上挥毫,记录下了那些戏曲的文辞、形象。当我们在龙山下的张桂铭艺术馆摇着一柄柄扇子,俨然“镜子照镜子”——扇中有画,画中有戏,戏中有扇——在一个纸面的剧场里,完成着一种奇妙的互相表现。

顾迎庆 · 寻梦
或许,打开扇子的那一刻,我们还能听到沈梅冈在时间囚笼里剖竹制扇的沙沙声,看到陈洪绶不胜酒力终究未能画下的白扇面,以及龙山夜雪里像花一样簌簌飘落的花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