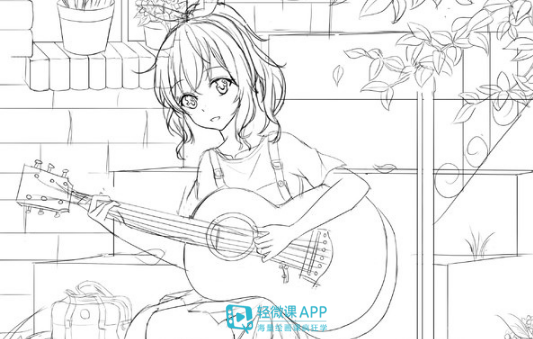以器物之名——当代陶瓷创作观念的变迁

▲碎岁(陶艺) 陆斌
器物是陶瓷存在最普遍且最丰富的形式,很长一段时间,它几乎固定了我们对陶瓷的认知。而上世纪60年代受西方现代艺术影响,陶瓷从器物入手,却以反器物的观念引发陶艺革命,从而改变了原有的认知。
从器物到反器物,根本上是材料的本质属性被重新挖掘,长期以强调功能性为主导的陶瓷设计观念,开始被制作者以强调主体意识和情感表达及新的审美追求为导向。这场关于现代陶艺的革命,由20世纪60年代美国陶艺家彼得·沃克斯倡导。他的陶艺作品保留可辨识的器物外观特征,却摒弃制作这类瓶盘碗罐所必需的技术规范,借由黏土的可塑性,对其进行刮、擦、撕、扭、压、印等行为,将器物视作一个可传达作者情感意识的表现性载体。这一行为颠覆了陶瓷传统审美,并对陶瓷功能性本质和因其产生的一系列美学和技术要求提出质疑。你可以说沃克斯的陶瓷是粗糙不美的,但它是真实的,保有泥土质感的。那些扭曲、撕裂、堆叠的形体,有着长短深浅不一的划痕或坑坑洼洼的表面,让人感受到不同力度的较量、各种情绪的交织以及时间速度的呈现,这是以往陶瓷所看不到的。这种主观意识的表达并不仅仅是一种情绪化的存在,更附有作者对某种僵化的陶瓷制作的反省和渴望重新赋予其活力的动机。
器物当然永远会是陶瓷创作的一种形式,然而反器物的观念和制作却带来了陶瓷的无限可能性,不仅打破了对器皿的看待方式,也发展了器皿造型本身。德国陶艺家露丝·达克沃斯的作品就常常将器皿与一些形体块面重新安排成一个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新鲜造型。她的作品有一种柔和、静谧、包容的气质,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改变着我们观看容器的方式,很自然地清除我们脑海中关于器物功能性的印象,而去感受它们抽象的魅力。不同于彼得·沃克斯陶艺的表现性,露丝所强调的克制美和对形体空间的处理,更加模糊了工艺与艺术的界限,不仅拓展了陶瓷的审美观念,也拓展了雕塑语言的表达。
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刻影响帮助现代陶艺不断完成形式上的拓展,而后现代思潮对现代主义彻底摒弃传统的反省则使得陶瓷创作开始重新结合传统去思考和表达当下社会现实、文化现状等议题。涉足多种媒介的英国当代艺术家格雷森·佩里以他的陶瓷和异装僻而闻名,他是英国特纳奖开办以来首次以陶瓷作品获奖的艺术家。尽管陶瓷在现代艺术影响之下,从工艺美术跨越到纯艺术领域,然而仍被排除在主流艺术之外,因此当时获奖的佩里饱受争议。佩里把涉及个体、家庭、社会、政治、阶级、宗教、性等各种题材和现代生活领域的各式场景以类似街头涂鸦的方式绘制于大众常见的花瓶上。这些花瓶已远离对精致优雅生活的装点,而是对传统印象中属于工艺美术的陶瓷器物不能表达思想的观念提出了质疑。不同于陶艺家们所强调的陶艺本体语言和个性化的审美观念,当代艺术家更倾向于文化、历史、社会、现实等跨越艺术本体的思考,这对当代陶艺创作观念的多元化产生重要影响。
陆斌是一位在陶艺创作领域里极具实验精神,并一直关注陶瓷当代性问题的艺术家。与当下不少现代陶艺家力求摆脱陶瓷工艺的束缚不同,陆斌着力将技术最大化成为艺术语言和观念。他曾在《大悲咒》系列中借由对黏土材料和烧制技术的掌控,使特殊烧制成型的佛塔、经卷、瓷瓶在展示过程中不断自行碎裂、坍塌,化为尘嚣,这里面的器物被塑造成“空”的观念载体,演绎了一场无常幻灭。而另一组作品《碎岁》则以一种类似修行般的耐力完成一次次的成、住、坏、空的轮回。作品的起始是传统经典造型的紫砂壶,经过一番支离破碎和繁琐复杂的修复之路又归于一把把完整可用但带有修复痕迹的紫砂壶。一把壶回到了一把壶,这个看似徒劳的修复过程,好似不断地循环,“空而不空”。艺术家在整个修复过程中身体力行地去思考传统和反省个体,并在摧毁与重构中没有表露任何建立全新抑或超越经典的野心,看似一种谦卑的匠人所为却是作者多年养成的对传统精神的重新审视和审慎态度。
如果说陆斌一直在寻求技术和观念的平衡中拓展陶瓷的当代性,那么另一位陶瓷科班出身的、具有深厚陶瓷技术经验,却成功涉足多种媒介的当代艺术家刘建华,则一直将这种材料作为当代艺术观念的各种实验场和探索工具。刘建华早期的陶瓷彩塑作品《迷恋的记忆》系列中有不少器物与人物雕塑的结合,这里器物作为一种具有隐喻意味的道具出现。他试图摆脱西方艺术系统的那种深刻影响,以一种极简形式和东方思维进行创作,这种观念转变之下的创作反映出艺术家所进行的当代艺术与陶瓷的磨合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向,也显示这种磨合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
其中一组《容器》作品以传统器物的形式呈现超越陶瓷器物概念的观念表达。这组作品借鉴宋代器物特质,艺术家延续宋瓷美学中的极简形式和中国传统陶瓷审美“类玉”特质的追求,容器外部施以温润均匀的影青釉,在这种充满宁静平和的表象之下,却以艳丽且极难掌控的郎红釉烧制在器物内部,形成一种满溢的视觉感,这种强烈的视觉冲突使看似传统的审美意境中蕴藏着某种内部的叛逆。创作者去除了作品中的描述性成分,也不再以一种明确的寓意将符号指向主题,而是在一种抽象的形而上意味中展现作品的张力,在对当下艺术刻意追求错综复杂的观念性和标榜社会意识及批判性的反思中逆向而为,追求一种更为纯粹、含蓄、内敛的东方意境,看似平淡却意味深长,这对当代艺术本身也是一种充满内省和自律的思考。与此同时,创作者对细节的把握和追求也更为严谨,极简的追求背后隐藏着一整套严密的工艺程序,那些实际不具备任何使用功能的容器却呈现着传统工艺所追求的极致——细腻胎质、完整同心圆、完美的釉色呈现、无瑕疵的烧制要求,最后在一片不露声色的简洁平静之美中透出一丝不安与不寻常的视觉和心理感受。
可见,陶瓷器皿所具有的强大传统背景并没有成为艺术家对其进行不同层面的思考和创作的障碍或束缚,而是构建新经验的开始,他们都以各自的成功实例呈现了观念在创作中的导向,以及当代陶瓷创作观念的变化和复杂面貌。
(作者系景德镇陶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