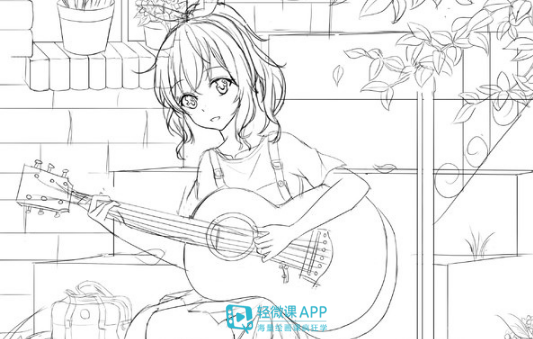又一次惊艳世人的三星堆遗址 有多少谜还没解开?
据“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3月20日通报,新近发现的6座“祭祀坑”内,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三星堆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的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1986年,1、2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其中不少造型独特、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
陈德安曾任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二十多年,其间主持过1、2号坑发掘工作。2019年12月,3号“祭祀坑”现世,他当时已退休,听到消息后仍赶往现场。得知3号坑填土和出土过重大文物的2号坑类似,陈德安就断言,“会有大器物”。
“这次发掘让三星堆与黄河、长江流域同时期文化的关系更为清晰。”陈德安近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三星堆文明不是独立起源的原生文明,而是深受夏商文明技术、礼制影响,并与长江中下游文明产生了互动。初步来看,新出土文物为此提供了新的证据。
与此同时,仍有一些谜团待解。与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年代接近的殷墟遗址(商朝后期都城遗址,公元前1319年—前1046年)已有成熟的文字系统,为何三星堆仍未见文字?青铜技术从中原传入成都平原后,三星堆这么多工艺高超的艺术品是在哪儿制作的?其原材料从哪儿获得?这些尚待进一步发掘、研究来求证。
“没有证据证明三星堆与古西亚、埃及等地有文化交流”
学界普遍认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中原夏商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三星堆遗址中由玉琮、玉璧、玉戈和牙璋演变成的仪仗用具和青铜尊、青铜罍、铜铃等,都是中原地区的风格。这些风格的遗物,基本上是在夏王朝后期都城二里头遗址形成,有相当一部分被商王朝所继承。
此次3号坑出土的青铜大口尊、方尊等器物,都是商代常见的青铜器,尽管它们在具体纹饰上有所差别。更为直观的是,新出土文物的“鸮”形尊,系三星堆首次发现,而在远在千里之外的殷墟遗址,同样有“鸮”形尊。
“这次最新发掘出来的部分文物,都和商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陈德安告诉澎湃新闻。
比如,三星堆早期的青铜器,和早商二里岗文化、殷墟初期的青铜器、河北藁城商代青铜器风格相近;特别是一些包括兽面在内的青铜器、玉石器和建筑基址的做法,更接近早商二里岗文化;比三星堆更早的良渚风格玉石器,也出现在了三星堆、金沙遗址中。
“当然,这些青铜器、玉器的联系不是成品的流动,而是礼仪观念和技术的输入。”陈德安称,这也说明从早商二里岗文化时期到晚商殷墟文化时期,古蜀与商王朝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之间存在交流,除了商王朝的政治、礼仪影响了蜀地以外,他们还有技术、资源方面的交往,如青铜器冶铸和玉石器生产。
陈德安称,古蜀文化对外交往中有向东向北两条路线,向东是从三峡地区进入南阳盆地,再到中原地区;向北是通过随枣走廊进入南阳地区,再到中原地区。他解释,中原文明同时影响着古蜀和长江中下游文明,而成都平原和长江中下游之间又有互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三星堆文明”。“在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往中,夹在中间的巴文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陈德安认为,商代的巴民族在蜀与商王朝的交往中起到媒介或驿站的作用。
按照不同风格,陈德安将三星堆遗址中的青铜器分为三类。“第一类风格接近早商的二里岗文化到晚商的殷墟文化,第二类则具有长江中下游和成都平原文化共有的一些因素,最后一类则是纯粹的本地特色,比如风格独特的青铜面具、纵目面具、青铜大立人像、神树、金面具等。”陈德安说。
也正是纵目面具、大立人像等“明星”文物的奇特外形,让一些网友将三星堆文明和域外文明联系起来。“从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没有证据证明三星堆与古西亚、埃及等地有文化交流。”陈德安称,古代的自然宗教产生于自然现象,古人看到自然现象是相同的,崇拜的对象也相同,他们塑造的神灵有相同或相似的方面,也很正常,“文化联系要看文化的基因,不是看表面现象。”
祭祀器物被集中掩埋,专家猜测系“掌权者更迭”导致
此次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注意到,三星堆的大部分器物都曾被砸坏或烧损,此外8号坑发现表面平整的五块石板、被火烧过的土块,而4号坑和3号坑里出现灰烬以及碳屑。三星堆遗址发掘执行领队冉宏林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根据这一系列现象猜测,这些器物或许都来自另一个祭祀场所,因某种原因建筑被烧毁,房屋倒塌后器物被转移分坑掩埋于此。
此前,不少学者根据三星堆遗址1、2号坑判断,这些坑是一次性形成的,属于“亡国器物掩埋坑”。但此次最新发掘的4号坑被证明属于商代晚期,比1、2号坑更晚,这意味着这些坑的形成有先有后。
“大家倾向于认为这里是古蜀国从殷墟早期到晚期的一个祭祀物品埋藏区。”陈德安告诉澎湃新闻,8号坑中发现了建筑物构件等,一些坑中还可能包括烧燎产生的灰烬,这进一步说明了三星堆遗址6个坑的形成,有可能是宗庙被废弃后将庙里的器物迁出,在庙外以某种仪式的形式砸坏烧燎后埋下的,“大家还是比较倾向认为从庙到坑的过程行为具有仪式性,属于祭祀坑”。
陈德安猜测,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现前述现象,或是缘于掌权者发生变化后,新任掌权者将前任掌权者的祭祀器物集中掩埋。他认为,三星堆文化影响范围颇大,成都平原、重庆涪陵长江沿岸、嘉陵江流域、涪江流域、大渡河流域等都发现了与其相关的遗址,这些地方活跃着不同的部族。
“三星堆是古蜀国的政治中心,有不同的部族在这个政治舞台上掌过权——虽然大家可能都来自同样的始祖,但在宗庙祭祀时仍会选择血缘更近的先祖来祭。”陈德安认为,正因如此,新一代掌权者推翻前代政权后,或将其用过的祭祀器物“毁掉”。“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就烧了、砸了、埋掉,而是会举行特定的仪式来替换宗庙祭祀器物。”陈德安称。
器物被破坏后掩埋,这也为修复工作带来了难度。文物修复大师杨晓邬有“三星堆文物修复泰斗”之称,虽然他已退休多年,修复工作由“徒弟”们接班,但最近一段时间,他仍忍不住去发掘现场转悠。“每件文物氧化锈蚀程度不一,修复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会耗费很长时间。”杨晓邬说,1、2号坑出土的文物,部分至今还未修复。
“从这次发掘情况来看,很多祭祀器物被敲碎,甚至焚烧,然后埋在坑里,层层夯土,毁坏很严重。有的就干脆被烧变形了、熔化了。”杨晓邬称,比如最新出土的残金面具,已是“半熔化”状态。据他介绍,此前他带着徒弟修复“青铜神树”,共花了7年时间。
三星堆与金沙文明曾经“并存”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同在成都平原,仅相距约50公里,因为不少出土文物风格近似,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常被学界所关注。此前,因三星堆仅发现了1、2号两个坑,不少考古学者判断系三星堆发生“内乱”,居民匆忙将文物掩埋到坑里后,然后迁都至金沙,导致三星堆文化消失。而此次发掘中新出现的一些证据则推翻了这一“假设”。
金沙遗址博物馆陈列保管部主任黄玉洁告诉澎湃新闻,从三星堆遗址最早的1、2号坑到最近几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来看,其和金沙遗址具有非常多的相似性,这一点毫无疑问。
“比如这次最新出土的这件残金面具,就和我们金沙遗址的金面具,风格非常接近,古蜀人以最尊贵的黄金做成面具,然后在祭祀仪式中使用,将其作为人、神沟通的媒介。”黄玉洁称,这从侧面进一步反映三星堆和金沙这两个遗址文化上的一脉相承、吸纳融合。不过,也需要意识到,两个遗址之间出土的文物有相同性,也有不同之处,“金沙是在继承三星堆文明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发扬和一些改变”。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联合北京大学对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其中4号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左右。这印证了三星堆新发现的4号坑碳14的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
金沙遗址博物馆遗产保护与研究部副主任郑漫丽认为,金沙文明兴起的年代距今约3200年,“三星堆尤其是4号坑现在公布的年代分布,有助于我们去清楚地认识到三星堆和金沙祭祀活动开展的时间,实际是有一段并存的关系。”郑漫丽称。
“三星堆和金沙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地方作为政治中心完结了,另一个地方才兴起。”陈德安告诉澎湃新闻,三星堆是古蜀国重要的政治中心,“贯穿了整个商代”,而金沙则很有可能作为“次中心”存在,“从三星堆分裂出来的”。“而这个次中心到底是因为‘内部斗争’导致的分裂政权,还是三星堆古蜀国主动向成都平原南部发展特意设置的结果,或者是其它什么原因,则有待进一步研究。”陈德安称,原来将三星堆、金沙作为两种近似文明的说法,“现在来看是不大对的”。两者文化传承基因是一样的,器物形制几乎一致,因此都属于商代以三星堆为政治中心的古蜀文明。
陈德安介绍,周灭商后,三星堆、金沙的商代蜀文化架构被西周文化打破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在以金沙遗址为中心的成都地区的西周文化遗存中看得比较清楚。从西周开始,古蜀文明的中心在金沙,成都作为地域政治中心的时间也要从这时算起。
“三星堆新近发掘的文物和新的发现,会对后续厘清三星堆和金沙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更多实物例证。”黄玉洁告诉澎湃新闻,这也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成都平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古蜀文明晚期之间的文化发展脉络。
三星堆遗址中的象牙可能来自本地
同1986年的三星堆遗址发掘一样,此次发掘也在多个坑中发现了“象牙”。而在金沙遗址中,同样出土了数以吨计的象牙,且根据检测,这些象牙来自亚洲象群。
黄玉洁告诉澎湃新闻,象牙被有规律地摆放在坑中,这很可能反映了其在古蜀人的祭祀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能是古蜀人献给神灵的重要祭品。黄玉洁称,成都平原早期河流泛滥成灾,而象牙在古人眼中有镇杀水中精怪的作用,因此用象牙祭祀可能是古蜀人在精神上的寄托。
黄玉洁介绍,金沙遗址中出土的一件玉璋上,刻画了一个古蜀人肩扛象牙祭祀的场景,这也为考古学家研究古蜀人当时的祭祀活动,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实物研究资料。而三星堆遗址2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双上一上一下,手掌合拢似握有物品,有学者就猜测这是古蜀人双手紧握象牙祭祀的场景。
这些象牙来自哪里?此前曾有学者认为,这些象牙或是通过与印度等地文明的贸易而来。对此,黄玉洁称,仅金沙遗址就曾出土数以吨计数的象牙,从外地交流而来不太现实,因此遗址中的象牙或来自本地象群。
据她介绍,古蜀时期的气温应该比现在要高,当时文献中也曾记载中原地区有大象的存在。此外,考古人员在金沙遗址还发现了大量极占优势的草本植物遗存,这意味着在当时,至少成都平原一带可能还属于热带和亚热带的温暖气候,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大概2摄氏度。
黄玉洁称,成都平原目前已出土了有大象牙齿、下颚骨以及象牙,虽然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大象身体其他部分,但考古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以后还会不会发现更多的证据目前尚未可知。
能否发现文字?“三星堆工厂”在哪?
三星堆遗址中出现大量青铜器、玉器等文物的8个祭祀坑,形成年代与位于河南安阳的晚商殷墟遗址相近。殷墟因出土甲骨文而闻名于世,但三星堆遗址迄今尚未发现文字。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此前表示,对于此次三星堆遗址发掘,其最期待的便是能在出土的青铜器上找到文字。
3月20日的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新闻通气会上,考古队领队冉宏林回应了许多人都关心的三星堆是否发现文字的问题。他说,现阶段三星堆考古勘探没有发现确切文字,但在陶器上发现了相关刻画符号,“我们倾向于相信三星堆遗址是有文字的”。
金沙遗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称,在三星堆的时代,中原文明也是才出现文字,所以彼时三星堆可能还没有文字。但在三星堆以后的文化中,比如“十二桥文化”,或者说“金沙时代”的人,应该掌握了文字,因为他们跟周人有接触。
有专家猜测,之所以三星堆现在还没有发现文字,或是因为古蜀人都把字写在比较容易损毁的器物上,比如木器、纺织品。此次发掘中的确发现了“丝绸的痕迹”,其出现在祭祀坑的灰烬层里,以及部分青铜器周边,似是用作包裹。
同样没有踪影的还有三星堆“青铜器作坊区”。三星堆修复大师杨晓邬告诉澎湃新闻,不同于中原,三星堆青铜器制作时没有“模具”,而是一件一件地单独打造,因此包括“纵目面具”在内的不少青铜器文物都有“补铸”痕迹。
“(青铜器)铸造完后,或是有一些破损,或是铜水没有到达,但重新铸造费时、费工,古蜀人就干脆用补铸的方法来进行修补。”杨晓邬说,这也能说明,三星堆青铜器铸造是在当地或附近某个“工厂”完成的,尤其是一些大件青铜器,很难从成都平原以外的地方运来,但“工厂”究竟在哪,“还没有找到”。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接下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手工业作坊区,尤其是青铜器的作坊区。”此外,还要寻找相关的祭祀场所、古蜀王墓葬区等。
据澎湃新闻了解,3月29日,正在发掘中的8号坑陆续发现表面平整的五块石板和被火烧过的土块,以及椭圆形的碳化木料。考古人员推断,8号坑是第一个与祭祀建筑有明确相关的遗存。但真正的祭祀场所在哪里,尚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