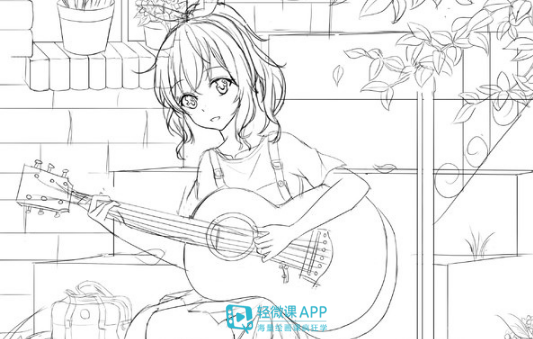刘成瑞行为、表演急评
不去现场看刮子的行为表演就发言是很荒谬的。但我的感触绝对真实,哪怕在他人看来是荒谬的。刮子的一系列行为作品让人眼前一亮,我不过是通过电脑翻阅他发给我的资料——一些他作品的文字和图片。严肃,刮子是位严肃的艺术家。不说别的,单就严肃已让人刮目相看。在礼崩乐坏、世风日下、很多人依然沉迷于泼皮调侃的时代,严肃异常珍贵。
行为之外无艺术。行为在前,艺术在后。艺术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行为。所以说,无行为不艺术。我不太愿意把行为和艺术这两个词拼在一起。但实与愿违,大部分人的行为总是被虚无的概念所框定。这里我不称刮子的作品为“行为艺术”,而直呼其行为、表演。历史告诉人们艺术只与风花雪月和技术有关。但那是虚假的历史,艺术倘若不与严肃和沉重关联,它根本不会活到今天。不是作为艺术的行为,而是作为沉重行为的艺术。
刮子让我想起一个人——被诸神处罚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又滚下山去的西西弗。刮子的行为、表演是一种自我惩罚或他罚吗?但真实的西西弗是一个抗议者。正如加缪所写的:“西西弗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还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他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这必然使他受到难以尽述的非人折磨:他全身心地投身于没有效果的事业之中。而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土。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惟有对西西弗才形成了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西西弗神话》)。存在是赤裸裸的荒谬,痛苦和幸福不过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表述。
“行为作品《一轮红日》是艺术家在2009年开始策划的一个方案,经过多年的累计和沉淀,终于落地。穿透锁骨是刮子小时候的记忆,印象中是对犯人的一种控制。现场空旷的空间没有多余的元素,一整块2吨重的巨石放在展厅一侧,沿着墙边的阶梯往上,一轮红日高挂在墙上,全身涂上赭石色的艺术家坐在展厅中间,专业人士将两根小拇指般粗的钩子穿过艺术家的锁骨,并与从天而降的红色丝带系在一起,之后艺术家便开始实施行为艺术,他用地上放置的大小不一的榔头,敲碎石头,并将碎石挪移到展厅另外一侧,有秩序地摆放,然后再取工具碎石,并挪移,由此形成的一系列的重复劳作构成了其行为的主体,直至展期结束。在整个行为过程中,艺术家面无表情,麻木地承受着外来的一切痛苦与束缚。他不讲话,也不离开自己的土地。他的休息地是在‘红日’上,不睡觉不休息的时候,他在工作,分解一块近2吨重的巨石,直至这块巨石被完全分解,或者没有完全分解而展期结束。艺术家希望分解后的每块石头都能找到一个主人,并以生者之名命名,费用是他工作的酬劳。”(引自《艺术客》)“一轮红日”是诸神吗?刮子的手中多了些许铁锤,他的目的是敲碎巨石,他可以休息,他可以随时停下来。“敲碎巨石!敲碎石头!”时间和记忆让人觉出了宿命的味道。
这依然是一个党派、国家、制度、市场、体制、主义、集体无意识等的时代,而非人的时代。获得人的主体性仍然是一个难题。艺术家应该为获得人的主体性努力吗?自由总是如天边的一轮红日,可望而不可即。而坐在一轮红日上喘息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西西弗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试问:最高的虔诚该献给谁?
2015年8月8日于绵阳芙蓉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