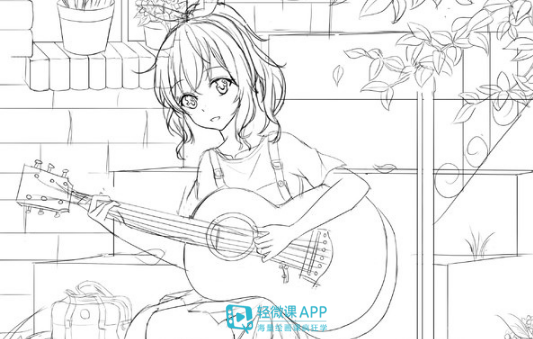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魂兮归来”吴为山雕塑的史诗
导言:2019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2周年,也是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为表达对死难同胞的哀思,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辜死难者,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国际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在2005年-2007年期间创作、落成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主题雕塑》,成为了我们铭记历史、寄托哀思的载体。这是一组记录历史的雕塑,让观看者勿忘国耻。这一组大型群雕真实记录了大屠杀中南京人民“家破人亡”的惨烈,呈现了手无寸铁平民的悲惨经历,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更让生活在当下的人们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

吴为山教授全然忘我,激情投入,经常躺在雕塑架下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吴为山: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
我接受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创作设计大型组雕是在2005年12月15日,是“大屠杀”祭日——12月13日的两天后。
时值寒冬,北风凛冽。我心情沉重仿佛时间倒流到1937年那血雨腥风的岁月,那逃难的、被杀的、呼号的……那屠刀上流下的鲜血正滴入日本军靴下……我恍惚走向南京城西江东门,这里是当年屠杀现场之一。白骨层层铁证男女老少平民屈死于日军的残暴里。而今纪念馆扩建又在地下挖出一批尸骨。虽然这一带已是住宅群立,各机构新楼布列。但冥冥中不乏阴风、冤气。极目西望长江滔滔,平静中有巨大的潜流,俨然三十万亡灵冤魂的哀号。自一九八二年我求学来到南京至今的二十多年间,我常常陪友人,国际来访者甚至日本同行来此凭吊。我们也常常可看到日本人士抱着忏悔和赎罪的态度在献花。我觉得这是每位有良知的人类一分子应有的历史态度。这种带着人性真善情怀而生发的悲剧意识是人类和平的心理基础。

《家破人亡》
我曾于2005年4月樱花时节应邀访问日本东京并举办雕塑绘画展。作品中内蕴的汉风唐韵感动着一衣带水的邻国观众,他们依依抒怀,谈及唐僧鉴真,也论到当年徐福率众男女东渡日本求仙草之往事。文化渊源的共通当获得彼此的理解。然,也有不解,《朝日新闻》记者问,六十年过去了,中国为何还不放过“大屠杀”事件!
我的回答只能是:以史为鉴,则后事可师矣。
摆在面前的是,尽管当年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皆以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争罪犯作了正义的判决,仅东京审判就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4336件,英文审判记录48412页,判决书厚达1213页。可是战后60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基本上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辞或躲躲闪闪的态度。其极右势力更是否定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不仅对战争不反省,对被侵略国家不道歉,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虚构”的,是“谎言”、“捏造”。每年的8月15日都有许多官员包括内阁大臣等去靖国神舍参拜。甚至小泉纯一郎连续坚持参拜供养着东条英机亡灵的神社。1996年8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部书,实际上是对侵华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全面的翻案。

《逃难》1
一个公然敢于推翻铁的史实的国家,及其右翼人群,是未来和平危机的隐患。
我们再看看国内状况,二十多年的经济建设,社会转型,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年轻一代的历史责任感普遍淡化,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已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人文理想和精神生命价值实现的需求;民族与国家的意识在个人主义膨胀中也渐渐模糊。曾经有一份报道,一批“明星”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边看着受害者名字,边笑着喝矿泉水。这张照片鲜目地登在《扬子晚报》,再看看图片文字说明,更是让人触目惊心!一个民族的子孙对自己民族历史灾难、耻辱竟如此冷漠,这种危机应当是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类似世界近代史上的三大惨案——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南京大屠杀,在未来人类会重演乎?在当今和平环境中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悚人听闻,但细想则是令人忧心忡忡。
因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程的扩建是历史的需要,是人类的灵魂工程。扩建工程首先是建筑,它是载体,也体现精神。史实——物证陈列是基础。作为凝固历史,铸造国魂的雕塑则是直接进入人心灵的。它为人们对客观史实的认识提供价值判断之参照。

《逃难》2
如此重大的题材,如此重要的地点,如此壮观的场馆,雕何?塑何?雕塑者何为?!
首先是立意,立意的基础是立场。是站在南京看待这座城市的血泪,同情当年市民的苦难遭遇;或是站在国家民族的方位,看待吾土吾民所蒙受的劫难?我认为只有立足于人类、历史的高度来正视、反思这段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的兽行,才能升华作品的境界,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纪念、仇恨。回顾一下我国自上个世纪至今所有表现抗战题材的作品,几乎是再现场面。那种国仇家恨溢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是时代的必然。但今天的中国日益强大,今天的世界日趋文明,中国有自信来倾诉历史的灾难与蒙受的污辱。作为受辱者,中国有责任控诉战争,有责任告诉世界,和平是人类精神所栖。一个遍体鳞伤的弱国是没有能力祈求和平的!因此凝固平民悲怆的形象,表现祖国母亲蒙难,呼唤民族精神崛起,祈望和平应当是整个作品的表现核心。立意明确后,要解决的是作品的取材与形式。

《逃难》3
有许多建议几乎是一致的意见:入馆处表现屠杀的惨烈,尸骨成堆,尸横遍野。主建筑下面血染成河。我则认为,纪念馆处于街区,在喧闹的现代商业、人居环境中,世俗生活情感与惨痛历史悲剧之间需要过渡。雕塑应当一目了然而又层层引人进入,悲情意识由内而生发。因此,叙事性、史诗般群雕组合可产生这样的感情交响,波澜跌宕,起伏壮阔。它超越一般意义上灾难的描述,痛苦的诉说,在这史诗中所生发的美,足以鞭挞丑恶、罪恶,足以从灵魂深处渗入,而荡涤人类的污浊。它有别于单一化、极端化、政治脸谱化的捏造,而是以普遍人性为切入点作深刻的表现。所谓人性是以人的生存,生活的基本生命需要、以人的尊严为出发点。

《逃难》4
在这恢宏的精神意象辐射下,一个强有力的旋律在我内心油然而生:
高起——低落——流线蜿蜒——上升——升腾!
它对应着:体量、形态、张力产生的悲怆主题《家破人亡》(11米高),继而是各具神态、体态、动态的《逃难》群雕(十组人物)。再继而是由大地发出的吼声,颤抖之手直指苍天的《冤魂呐喊》(12米高抽象造型)。
这组组雕的背景是以三角形体面为元素的主体建筑为背景,组成激越而低沉,悲惨而激愤的乐章。就空间而言,它形成气场,使观众统慑于悲天悯人的氛围中。在进入纪念馆前已受到净化。让观众进入纪念馆后,每见一根白骨,每见一件血衣产生无限的悲情和联想。
优秀的创作设计方案是思想的体现,但只有成为公共艺术,走向空间,落实为物化后的精神载体,才能称为作品。当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感染了观众,化为心灵的寄托,才是真正的存在,其价值也才能得到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方案的评审通过至关紧要。否则无以实施。评审是复杂的,比创作更为难。他涉及到所有专家评委、所有领导的审美眼光和对作品立意的认同。与建筑相匹配的雕塑,其方案通过与否,建筑师往往首先取得话语权。一般的争论焦点会集中于尺度方面。建筑师强调的是建筑主体,雕塑只是点缀的装饰,或是配角。雕塑家则强调雕塑的纯精神意义和艺术的直接感召力量。

《逃难》5
我预感到所创作方案的评审难度。决定以三种表现方式呈现方案,全方位、立体地让专家、领导了解。并试图一次性通过。根据我的经验,若一次性不能通过,再根据诸多意见进行修改的话则遥遥无期,且方案的风格,特点会不伦不类。
这三种呈现方式首先是创作方案的图片,配文字说明;其次是电脑图象漫游,配音乐,旨在使观者情感随图像漫游;再次是按建筑与雕塑实景比例缩小,制成大型模型,配灯光,使观众身临其境。第三种方式所付出的人力物力是巨大的。我寻找到一个未落成的美术馆大楼,在大厅里作了80米长的模型,主题雕塑模型做到6米高,营造了一个实景空间。2006年九月份,省委组织了全国十多位专家评审。他们在这样详尽的方案面前受到了震撼。主要领导根据专家意见,也表示:实施过程中保证方案的完整性。

《逃难》6
方案得到一致好评,通过了!
然而,正如我所预料,原设计主题雕塑12米受到了建筑师的反对,因建筑师规定只能为5米。相持半年,我的创作初衷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其核心是“遇难、纪念”。它的第一主题应当是《家破人亡》,且以12米的高度,表现被凌辱的母亲悲痛之极,无力地手托着蒙难的儿子麻木地向着苍天呼号。屈辱而不屈。她是千千万万受难家庭的代表,是蒙难祖国母亲的象征。造型似大写的“人”,嶙峋而沧桑的身躯在视觉上给人以震撼,带着这样的震撼缓缓移步纪念馆的大门。

《逃难》7
长长的路当成为观众凝思与纯化心灵的流程,该雕塑的创作手法采用“大写意”,让母体成为山河、成为巨石。且配以诗文:
被杀害的儿子永不再生
被活埋的丈夫永不再生
悲苦留给了被恶魔强暴了的妻
苍天啊……
作品中所塑造的母亲双脚,赤足于大地,痉挛欲绝、那已永不再生的儿子化为了山脉。著名建筑大师齐康院士在现场认真比较18米高建筑与雕塑的关系后,断言:雕塑不能低于11米。与我的设计吻合!而今落成后的这尊标志性雕塑,让过往行人望而生悲,让走近的观众如临巨岩,产生强烈的压抑感。

《逃难》8
我常常在思索,如真的存在灵魂,那当年的受难者会是怎样地告诉今天的人们,他们身心的创伤?!我曾访问遇难幸存者常志强,这位亲眼看着自己母亲被日本人刺死,亲弟弟泪水、鼻涕与母亲血水、奶水冻凝一起。时光已逝去七十个年头,可这位八十岁老人仍然声泪俱下,噩梦未醒。我有一个强烈的欲望,要复活那些受屈的亡灵。纪念馆内那些头盖骨上的刀痕,那被砍断的颈骨,那儿童骨头上的枪眼……,那在光天化日下被剥光衣服的妇女的哀哭,身上还投射着日本军帽的影子;那被反绑着双手、跪着,刹那间,身首已分的俘虏;那被集体活埋的妇女、青年,在日本兵铁锹覆土的间隙,昂首不屈的男子……,在我不平静的创作遭遇里,无数彻夜难眠的夜。我甚至走在南京旧城区,也不自觉听到轰鸣与刺杀的哀鸣!试想,纪念馆的大门就是攻陷的中华门,如果每个进馆内的人,相遇了这批由城内而逃出的亡灵,这当是历史与现实,幻觉与真实,灾难与幸福,战争与和平的相遇。我将这10组21个人物置于水中,与行人及建筑若即若离,营造时空的对语。尺度近乎真人,从感觉世界里与观众互为参与。他们中有:妇女、儿童、老人,有知识份子、普通市民、僧人等。最为让人悲怜的是常志强的母亲将最后一滴奶喂给婴儿;最为勾起回忆的是以儿子搀扶八十岁母亲逃难的历史照片为原型的创作;最为令人惊恐的是那被日军强奸的少女为一洗清白而投井自尽;最为引人沉思的是僧人为死者抹下含冤的双目……。这二十一个人物,虚实错落形成悲烈的曲线。雕像为银灰的色质。迥然于见惯了的青铜、古铜色,它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空冤魂,是弥天恐怖中逃出的难者。

《逃难》9
这组雕塑我做得极为淋漓酣畅,它可以凭籍体态、动态的极端夸张而达到 极强的表现意念,可以将老人那颤抖的筋脉刻划得入微而生动。也可以从他们凸起的双眼揭示那惊恐与仇恨!在这里,精妙的写实和概括的写意,准确的塑造和变形的夸张,结构和比例的所有标准只服从于“表现”!这种表现是缘自于魂的底层又深入到骨子里的大表现!由此,我真正体会到结构与灵魂的对应;表现与精神的对应;夸张与情绪的对应。这组《逃难》原本设计是由数十组逃难者组成的人流,以造成气势,好象一下子从城中涌出来。但方案被评审专家给否定了。他们建议以少胜多,以每组独立的雕塑而概全貌。这是虚中的实象,是中国戏剧舞台的表现智慧。但落成后,也有另一批专家认为该用原先方案,以多取势,以多求逃难人群的丰富性。
历史上,无数艺术作品的个案证明,有些只有唯一的设计,往往妙不可言。有些可有几种设计方案皆能采用。一旦某种方案实施了,时间久了,也便成了心理上的唯一。

《逃难》10
建筑师为纪念馆设计的主建筑由东至西,最高处18米,最低处西端为正负零。我设计的《冤魂呐喊》在西端,从构思上步入情绪高潮,从整体视觉形式上呼应了建筑,也为建筑的西端增加了应有的平衡。它以劈开的山形寓意破碎的祖国河山,其豁口便自然成了纪念馆的门道。它虚拟城门,是逃难之门,是死亡之门。左侧三角形直指苍穹,塑造了一呐喊的冤魂。右侧表现的是平民生灵被屠戮的场面。它拔地而起,斜插云霄;是冤屈的吼声,是正义的呼号。以三角形的视觉冲击,紧连大地摄人魂魄,撼人心魂。
西方现代艺术革命,其重要的成果是以几何形体对事物进行抽象概括与情感进行抽象表现。突破单一写实手法对客观形态的描写。这一成果被广泛运用于设计,也常被纯艺术创作所吸收。但不免形式脱节于内容表现,略显装饰、单薄,在《冤魂呐喊》这组雕塑中,几何体的运用是我无意间在视觉幻念中形成的。它是从大地深处突兀而出的!我冥冥感到在那样的空间,在《家破人亡》、《逃难》后需要这样一个“大抽象”符号的感情特征而彰显,以昭观众。

《冤魂呐喊》
《家破人亡》、《冤魂呐喊》均是于天地间找到空间。室外雕塑最为重要的是借助于天地之势而造型,缘自精神表达而生发张力,依托于象征性而激发人们的迁想。主题性、历史性雕塑还应通过其体与量的相对关系展现其厚重与深刻。《冤魂呐喊》,将人间的苦难诉渚于上苍,分别为12米、7米的两个三角形体块将观众陷于其间,压抑狭窄的“逃难之门”为观众与“逃难者”塑造了同一的情感通道。

《家破人亡》
三组雕塑互为相关。为纪念馆拉开了历史悲剧的序幕。由此而入馆参观展程。
走出纪念馆,是和平公园,但见绿洲一片,在出口处长一百四十米,高八米的墙上以“胜利”为主题作浮雕墙。以“V”型为基本构成,分别以“黄河咆哮——冒着敌人炮火前进”“和长江滔滔——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为内容作浮雕。在“V”型的结点处塑造了一位吹响胜利军号的中国军人,脚踏侵略者的钢盔和折断的指挥刀。采用中国古代雕塑象征主义手法表现了人民的胜利、正义的胜利,也象征着让战争远离人间。该雕塑采用现代设计的构成手法,借助三角形“V”字的大小对比透视,形成气势宏宽的大场面。胜利的主题与《和平》公园主题相辅相成。放射状的浮雕有力的表现了胜利的精神状态,它仿佛拥抱和平的双翼。为一部悲烈、沉郁的史诗结尾处,找到了舒展而光明的警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航拍
整个组雕,没有出现一个日本侵略者的形象,皆表现我遇难同胞,表现我中华儿女。2007年12月13日开馆前后,有许多日本观众和记者在雕塑中专门寻觅他们先辈的形象。据说,中国文艺作品(尤其是电影)中所刻划的“日本鬼子”大令今天的日本人伤感。而在这组组雕中,从遇难者群像的惨烈足以佐证日军之凶残与兽行。日方记者无可挑剔,在于我们是以和平祈望而塑魂的。是为纪念我同胞而塑魂的。它的潜台词则为:
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

《胜利号角》
塑造手法中刀砍、棒击、棍敲与手塑相并用,其雕痕已显心灵伤痕,是民族苦难记忆,是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罪证记录。塑造的悲与愤产生速度与力量,在《辛德勒名单》的主题音乐的回响中完成每一个形象……38度高温酷暑的露天劳作,深夜连续十多个小时的创作已注定了艺术家情感和民族情感、人类情感的相融,并将此投射到作品。为此,我写下:
我以天地言状的悲怆追忆那血腥的风雨,
我以颤抖的双手抚摩那三十万亡灵的冤魂,
我以赤子之心刻下这苦难民族的伤痛,
我祈求,
我期盼,
古老民族的觉醒!
精神的崛起!

《胜利号角》
潘基文:“不仅表现了中国的灵魂,更表现了全人类的灵魂。”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评价吴为山教授的雕塑 “不仅表现了中国的灵魂,更表现了全人类的灵魂。”这实质是吴为山对中华民族、对全人类情感的真实表达和倾诉,为拉贝新墓的设计与创作,则表现了吴为山教授对爱国情怀的感恩和深深的缅怀。

吴教授塑拉贝
2006年,吴为山教授为位于南京的拉贝故居塑造了一尊“拉贝像”,在雕塑旁,吴为山教授曾不无感慨地说,“你看他(拉贝)的眼睛,从里面能读到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尽管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76年,但是拉贝先生为中国、为世界和平所做出的伟大贡献的事迹却一直为后人缅怀。1950年,拉贝在柏林去世,下葬于德国柏林西郊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墓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拉贝先生的墓碑被管理部门拆除。此后,墓地便一直没有任何标志,很多前往柏林拉贝墓地拜谒的中国人却发现,拉贝墓没有墓碑。

《拉贝像》
拉贝先生的新墓的主要设计、创作任务落在了中国雕塑院院长、南京大学吴为山教授的肩上。吴教授当即表示:南京人民不能忘记恩人,中国人民不能忘记恩人。中国艺术家有责任有义务有真情为拉贝先生塑像、立碑。他义不容辞接受了任务,并表示义务创作。他还邀请了他的好友单踊教授共同商议、研究。
拉贝先生的新墓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新碑基座嵌有南京特产的雨花石;多彩的雨花石象征着南京人民对拉贝先生的怀念与感恩。碑身选取了中国石雕之乡河北曲阳的花岗岩,并以黑白两色组成“N”造型,也表示着“南京”这个与“拉贝日记”有特殊关系的城市。在战争与和平、光明与黑暗的交接线上镶嵌吴为山亲手雕刻的青铜浮雕拉贝像,拉贝先生的身影和深邃的目光凝聚在这空间中,这石头城的历史中。
2013年12月11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雕塑院院长、著名雕塑家吴为山教授等无偿设计、创作的拉贝墓在德国柏林举办了墓园落成仪式,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德国外交部、拉贝先生后人等出席仪式并致辞。

《义勇军进行曲——聂耳》,青铜,高2米,2009
吴良镛:展现了人类罕见的历史悲剧,是雕塑的史诗。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法兰西通讯院士、建筑大师、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评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群雕》时称:南京是我的故乡,1937年南京失陷前我随兄长匆忙离开,而父母等只能留守。在我从武汉到重庆的路上,南京大屠杀的种种传闻不绝于耳,至今每当回忆起当时坐立不安的情景,心境始终不能平静。不用多说,我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先后两期工程成功的创作抱有特殊的感情。
我是二期工程评委之一,在审慎思考之后当时认定现在实施的方案以其与主题切合而入选。但当时对该方案也存有过闪念,即象征一把利箭端头的高大墙面及所在空间当如何处理?也未及仔细琢磨。建成后我有机会去南京实地参观,这一纪念性建筑可谓惊心动魄、扣我心弦。特别见到吴为山先生创作的“家破人亡”、“逃难”、“冤魂呐喊”的群雕,使拜谒者顿觉震撼。如以那组冷酷的高墙象征帷幕,将当时的人间浩劫展现在拜谒者眼前,仿佛又回到那悲惨世界。这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笔墨,只是苦难同胞在野兽奴役下的恐惧悲号与死亡前的挣扎,展现了人类罕见的历史悲剧,是雕塑的史诗。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主题雕塑之《逃难》吴为山教授创作
一般而言,作为纪念性建筑其表现力多寄予形体的庄严、力量、雄伟、宏大、朴实以及环境空间的塑造等等,以其相对抽象的形象表达出主题的内容和内在的美得蕴含——这极难能而又可贵。但它不能像文学作品可以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当需要有叙述性的表达时则往往借助于雕塑、题记、书法以及园林环境等多样艺术手段的集合。成功的作品不仅在于建筑艺术质量的水平,还依托于上述手段的综合构成,以简洁地将整个纪念物主题表达到完美的境界。如果在这些艺术手段的某一方向有独特造诣,就更能画龙点睛,为整个纪念性建筑物增添异彩,增强艺术的感染力;反之则易落于平庸,白白浪费创作的机遇,现实中这类事情时有发生,令人不胜惋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群雕独具意匠,个人风格独创,与主体建筑巧为融合,凡此种种。落成后反响强烈,所有这些就更能雄辩地说明了它的成功,而这正是纪念性建筑创作的难点所在。

《胜利号角》
杨振宁:仿佛听到了当年日寇飞机的轰炸声。
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评价吴为山“大屠杀”组雕: “看到吴为山先生所作的“大屠杀”组雕,令人震撼!仿佛听到了当年日寇飞机的轰炸声。那是永远刻在心灵的记忆。这组雕塑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一样,将载入世界美术史。”